“会讲潮州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胶地郎,打死无相咁”,“人情好,食水甜”,这是旧时潮汕人最好的写照。生动地反映当时潮汕人团结互助,无论你我,扬善除恶,一家亲的一面。面对海内外潮商在商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基于血缘和地缘认同之上的网络化经营,是企业管理学上的一场革命,而这种商帮网络的具体表现形态就是会馆等社团组织。表而上看,会馆只是旅外商人与乡土相联系的文化纽带,以“笃乡谊,祀神祗,联嘉会”为主要职能。但实际上会馆是一种地缘性的具有自助自保自治性质的社会组织,是商人群体间自觉进行契约和整合的结果。在商业活动中,会馆发挥着与传统宗族势力相类似的作用。

潮人以同乡间的团结、互助、互相间解危扶难而著称于世,这种强烈的地缘结合意识和同乡凝聚现象比比皆是。出门在外的潮州人喜欢称同乡为“自己人”,尽管他们彼此可能萍水相逢。

在许多潮商的创业史中,同乡的支持与援手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早期香港南北行的创始人高楚香、香港晋兴集团创始人翁锦通、著名的潮商汤秉达等都有过被同乡收留和得到同乡照应的经历。马化腾的腾讯在准备出售的最困难时期,得到李泽楷旗下盈科及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及时注资,才走出生天。

传统的潮汕社会是宗族和乡村重叠的“宗族乡村”,是一种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宗族社区。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并且对海外潮商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组织形式上,宗族组织主要是祠堂、庙宇、联甲和结社;在组织功能上,宗族的职能主要是族产祠祭、迎神赛会、族内法政和族外交涉。会馆也有着相类似的组织和功能,会馆本身就是类似祠堂的会所,是商帮的宗教和议事中心:清代吴县潮州会馆内设有“关帝君”,“天后圣母”的神位,泰国潮州会馆则代管老本头古庙和龙尾爷等神庙;会馆一般也都设有类似乡村结社的职能机构。然而作为工商社团,会馆的作用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内整合市场秩序,对外形成商业生断上。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仲裁商务纠纷,营造诚信的商业氛围,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在东南亚,潮商通过社团等宗族势力形成区城垄断的现象十分明显,米业加工运输和南北贸易基本由潮人控制。

在汕头市市郊个村里,有两所天后宫。明明是人们熟悉的海神庙,却用红纸横额盖在门楣上。一所天后古庙上写的叫”义盟公司”。这个“公司”却不是卖东西的,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看两旁的对联就清楚了:
义气同心同德
盟志共愿共酹
开首两个字就是“义盟”。这个庙就相当于联盟结义的公证处,于是我们明白为什么它要称“公司”了。在另一处天后宫,横额上写的是“忠烈社”。对联是:
义当所为准日酹恩践诺
烈其天职随时资友扶亲
这里说的就更为明白了,天后宫前的誓言主要讲潮人的互助精神。就是倡导潮人的互助精神,认为那种“随时资友扶亲”的作为是每个潮汕人的天职。这种相互帮助的精神,是由于长期海上生活所养成的,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潮汕渔民是以海作田的,尽管在陆地上有时也不乏“窝里斗”,但一到了海上,则“一浪泯恩仇”。相互帮助,同舟共济的精神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因为在浩瀚的大海上,再大的渔船落在波涛中也不过是一片树叶而已,危机和灾难时刻威胁着渔民们。在危难中最亲的,不尼远在陆地上的亲人,而是有缘相遇的最近船只。倘若遇上海盗,“红头船”也会自动靠拢,互相掩护,同共对敌。久而久之,潮汕渔民自己也武装起来,保护自身利益。尤其在明清时期,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不仅不能保护渔民的海上安全,反而常常下令封海。这等于断了渔民的生路,勇敢的渔民联合起来,占据海岛,实行武装割据。南到印度尼西亚,北到定海,都活跃着潮人为主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维系这种民间组织的精神力量,就是“忠义”二字。在北方,联盟结义,一般都要到关帝庙里,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为榜样,在海边没有关帝庙的地方,就把天后古庙临时改为“义盟公司”,总之,有神明作证明就行了。

海上商业活动所具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与陆上贩运所需的骡马锱重相比,从事远洋运输的海船投资巨大,多则上万两白银,可容百人甚至上千人,而且船上货物价值均在万两以上,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备任何武器),却不得不在海盗与波涛中穿行,其风险足以让人扼腕,但对于潮商而言,却只是“冒险射利,视海如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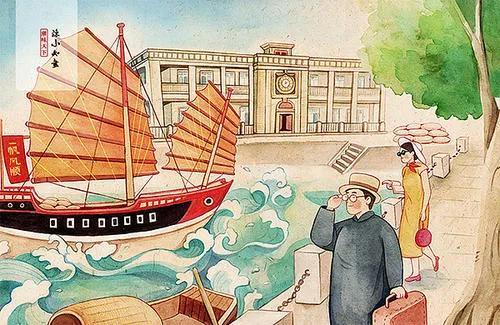
正是由于这种海上商业活动所具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大商人拥有巨资,他们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船主从中小贩商的商业利润中抽取商银,抽取程度按盈利大小计算,多赚多抽,不赚不抽。水手收人则根据船东抽银多少而按比例分成。
这种商业伙伴关系,便是潮商群体生长出商业信用及团体协作的最初萌芽。在近代中国社会缺乏法制化、规范化的工商业竞争环境中,面对强大的西方商人的虎视眈眈,潮商正是依靠其团体内部的信用得以发展壮大。
海上航行的凶险,明、清政府对其利益的漠视,海外求生的艰难,都使得潮商分外团结。而团结山为潮商在历次商战中,以小击大提供了最牢固的保障。
潮人靠这种互助精神,逐渐在海外生根,发展从点到面,铺展开来,相互携助,共渡难关,营造了对整个潮人经商有力的大环境。
比如一个村庄的人,有一个在海外站住了脚,有了发展的基础,村里的年轻人就可以“一条水布下南洋”去找他。可能并不认识,不要紧,你只要会讲潮州话,能说出你的父母、亲戚是谁,住家旁边有个什么特征,对方就相信你是个同乡或是同族人。如果你能带一点对方熟悉的家乡土特产,就更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了。所以潮汕至今管这种见面礼叫“手信”,就是信用的象征。主人认可后,你就可以在他手下白吃、白住,帮他做事,慢慢地找工作,积累资金,成家立业,直到自己开公司。一旦独立了,你也可以与主人开一样的公司, 也可以与他竞争,这叫“在商言商”。这是不是大陆文化讲的“恩将仇报”或“忘恩负义”呢?不是。潮语中有一句俗语“单仔勿食肉,单鸡勿食粟”,意谓没有竞争,胃口不开。竞争是讲公平的竞争,帮助归帮助,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要把报答主人提携之恩,转移给其他投靠你的乡亲身上。如果后来居上,挤垮了原来的主人,在生活上你有道义上的责任照顾他;在事业上,你有“资友扶亲”的义务,帮他东山再起。这是市场经济残酷的规则所决定的,“亲父子,明算账”,“在商言商”。表面上好像不近人情,实质上比大陆文化那种大家族里,表面上温情脉脉,暗地里勾心斗角,要明快得多。谁欠谁的多少情,心中更加明白,这样大家才好合作,把事业做大,潮州人在每个异乡他国,都能很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地方的“散兵游勇”,自然就可以稳操胜券了。这才能形成“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的局面,凡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商会。不要说东南亚各地了,仅就美国的潮州社团就有几十个。

潮人组织也有助于潮人资金的筹措、商业资讯的交换以及合股经营企业。历史上,海外潮人(甚至包括其他方言群体的华人)常通过宗乡会的组织,以一种独特的互助融资方式取得资金,这就是所谓“标会”。一般的“标会”由一群人(大约10到30人左右)来参加,每人每月缴交一定的款额, 带领“标会”的人称为“会头”。规定每月标一次, 标到的人便可获得所有的金额。标到人所填写的金额,即为当月其他个人所赚取的利息。参加“标会”的人虽然得冒风险,但对大家都有好处,出钱的人能取得比银行更高的利息:而标到会的人,并不需交付抵押品,却可借到钱,而付的利息比银行的还低。
宗乡会能促进彼此情谊,而俱乐部更能提供大家消闲的好去处,大家在茶余饭后,酒酣耳热之际,高谈阔论,交换商业信息。倘若彼此情投意合,具有共识,更可一拍即合,合股经营。
通过地缘与血缘关系,早期的新加坡潮州人也和外地同籍人建立了商业联络网。他们之所以能垄断新加坡的米入口业、陶瓷业及香汕郊(小商店)等行业,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其精明的经营手法,另一方面各地商人的传统渊源也产生一定的作用。新加坡的米粮多半来自泰国,而泰米几乎由泰国的潮州人所垄断,因此他们乐于与新加坡的潮人接洽、谈商,并予以人口与放账等方面优惠的待遇,使潮籍米入口商的经营处于有利地位。汕头、潮安与枫溪等地区盛产瓷器,颇负盛名,新加坡的潮人具备了地利与人和,顺理成章成为潮瓷的代理商与零售商。在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后,其余如江西的瓷器,石湾的陶器、日瓷与欧美各国的瓷器,也大都由潮人经售。至于潮人之垄断香汕郊与海屿郊等行业,也是由于地利与人和所使然。

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社团,这些社团包括会馆、商会、同乡会与各种艺术、娱乐、宗教、慈善团体等。目前仅在香港登记的潮汕人团体便达到了100多个,这是其他地方的人群所难以比拟的。这些团体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认同意识对于潮汕人经商有莫大的好处。初次经商者,老乡的帮扶及经验的传授使之能尽量少走弯路,并且在困难时得到及时的支持。经商者之间广泛的商业信息沟通与合作精神,更使得潮汕人在商人群体中鹤立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