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国打上半场,国外打下半场,中国留学生打全场。”在很多在外的中国留学生看来,这不是一句调侃,而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无法再进入的实验室、中断的毕业设计、抢空的超市、取消的航班、封锁的城市、各国民众对待疫情的态度……疫情之下,留学生在当地经历了世间百态。
他们之中,有人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小心翼翼辗转回国;有人选择在当地留守,陪心爱之人度过漫漫长假。这次难忘的经历,让这些留学生感受到人类命运紧紧相连,对生命、亲情,都产生了新的认知。
中断的毕业设计
英国一年制的硕士项目往往在四月中旬第二个小学期末结课。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硕士生林伶的不少同班同学早早订了回国机票,准备实习、找工作,待七月份第三小学期结束时再回到英国参与毕业设计答辩。
林伶打算第三学期留在英国做毕业设计,主题是制作一个伦敦电子地图。在她的构想里,电子地图的用户是到伦敦旅行的各地游客,地图可以为他们推荐伦敦当地人心中的美食。林伶是广东顺德人,纪录片《寻味顺德》火起来后,常有外地朋友到顺德旅行,寻找美食。好客的林伶只带朋友们去吃顺德人认准的老店。朋友们告诉林伶,虽然是外来客,有当地人的推荐同样能吃到最“正”的美味。
林伶来伦敦后也曾想寻找当地最地道的美食,但旅游网站上多是旅客的推荐,加上课业繁重,她很少有时间去了解普通伦敦人的生活。“整个硕士项目的学生里没有一个英国人,老师也来自世界各地。一年到头,总觉得自己对英国、对伦敦没了解多少。”
毕业设计给了林伶机会。制作地图需要林伶的团队进行大量的实地调研,了解目标用户的需求和伦敦城的实际情况。在她看来,这成为了解伦敦生活的绝佳机会。“我们要去做访谈,和很多普通伦敦人访谈,了解他们最爱伦敦的哪些部分。他们向游客推荐的才是真正的伦敦。”
然而,新冠疫情在英国蔓延,林伶只能暂停毕业设计计划。具体如何调整,还需要和老师、组员商量后再做决定。“不能做期待中的毕业设计,还挺遗憾的。”
“我不敢回国,我怕我上学期期末考试挂科,如果回了国,再回来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了。”朱赫是北京理工大学大四的一名学生,一年前,他报名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和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交换项目,计划在德国完成大四的课程及毕业设计。
3月中上旬是朱赫的期末考试周。“学习压力非常大,每天只睡五个小时,白天除了吃饭就是学习。哪还有时间想疫情的事啊?”
3月中旬,结束了最后一科考试的朱赫突然“蒙了”。彼时,德国已有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700余例,朱赫所在的达姆施塔特市也出现了确诊病例,他才从昏天黑地的考试中惊醒,“现在想想,挺后怕的,之前没做任何防护措施。”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德国的蔓延,朱赫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无法再按照原计划,每天去实验室跟随导师完成关于复合材料力学的毕业设计,而是居于家中看论文,以及自学一些工程模拟软件的操作,“现在肯定是做不了实验了,先多做做功课,希望疫情过去之后能提高研究效率。”
朱赫介绍,根据学校规定,他需要去学校的机械中心注册后,才可以开始毕设创作。然而,新冠疫情暴发后,学校就关闭了。“我已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完成了注册,同时,论文期限最多只有五个月,现在距离答辩只剩下三个月,每天都盼着疫情早点过去,我好回实验室继续做实验。”
“和我一起过来的还有几个同学,他们中有的人打算继续在德国读硕士,这部分同学现在已经回国了。”朱赫的导师和他说,一定程度上他有延期毕业的可能。而朱赫毕业后的计划是到英国攻读硕士学位,如果无法按时毕业,他后面的日子将会麻烦得多。
回与不回的纠结
除了毕业设计受到影响,这些在外中国留学生们也担心自己被感染了。
为了减少被感染的可能,林伶选择闭门不出。她住学校的宿舍,那是一个en suite(套间)房型,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大部分日常起居都可以在卧室中完成。但她需要和另一间卧室的同学合用厨房,这是她最担心的地方。 “疫情这么严重,室友依然照常出门,合用厨房难保不会造成交叉感染。”
学校在3月23日已经改上网课。林伶每天待在宿舍狭小的空间里,除了上网课再也无事可做。英国的疫情蔓延迅速,这让她渐渐有些焦虑。回国?目前已很难买到直飞的机票,多次中转、航程较长的航班势必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不回国?宿舍空间狭小,长期居家生活容易导致焦虑情绪,英国当地疫情也很难说什么时候结束。
权衡再三,林伶买了3月26日经由莫斯科中转的航班回国。当她收拾好行李,并将宿舍里储备的“存货”送给了其他人,等待回国之时,3月22日,俄罗斯政府宣布,3月23日起,俄罗斯将临时限制与所有国家的空中交通。除撤侨包机外,与每个国家仅保留一条航线。
这个消息让林伶所在的同学群炸了锅,她身边的中国同学有三分之二计划回国,不少人买了同一趟经莫斯科中转的航班。“打了好多电话,但是对方就是不回应是不是要取消航班。”与此同时,不少国家也开始对非持有本国护照的旅客进行入境和转机限制,一旦中转莫斯科的航班取消,留给中国留学生们的选择只有全程超过三十小时、中转两到三次的航线“曲线”回国。林伶等人把这样的航班称为“死亡航班”,“大家回国都是全副武装,尽量避免吃东西、喝水、上厕所,三十个小时的航班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们肯定会虚脱。”
“最好的情况是从莫斯科回国的航班没有取消。即使取消了,希望还有航班把我运回伦敦,好歹还有个睡觉的地方。”林伶说。
“现在剩下五张票,你要不要收拾行李马上回来,快点答复我。”3月15日,美国福特汉姆大学硕士生邱邱接到母亲的电话。而前一天,福特汉姆大学宣布了线上授课将持续到春季结束的消息,此时回国对邱邱来说,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
“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但没有想到我要去面对它。”邱邱的男友一脸平静又疑惑地望着她。看着他的眼睛,邱邱始终没办法对电话另一端、位于大洋彼岸的妈妈说一个“好”字。“如果我走了,我跟这个在乎的人是不是就这样分开了?”
挂了电话,邱邱心里第一次有了不知所措的慌张。彼时,纽约大部分学校已经停止线下授课,大部分公司已经实行在家办公。超市里肉蛋奶每天都几乎被一扫而光,邱邱订购的食物送到手里的只有不到10%,口罩等防护物品基本买不到。通过小区的邮件,邱邱得知她所住的楼里,也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如果现在不走,会不会有食物买不到,交通封锁,想走走不了的那一天?如果我被感染了怎么保证存活条件?”邱邱陷入了纠结,但最终她选择留守纽约。作为金融专业学生,她一边盯着金融市场在病毒危机下呈现的全球震荡,一边读着一本讲逆境中成长经历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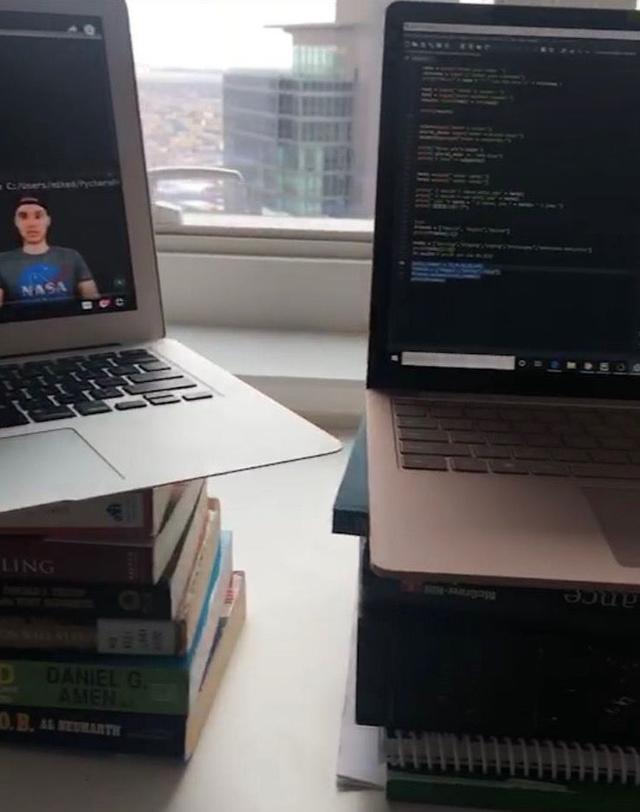
3月14日,邱邱所在的福特汉姆大学宣布线上授课将持续到春季结束,邱邱每天在宿舍里上网课。受访者供图
回国的安与不安
3月15日,蔡晓从加拿大温哥华回到了祖国。蔡晓运气不错,买到了直飞航班,航班在厦门降落,蔡晓填报完身体健康状后再乘另一航班到最终目的地——山东济南。
蔡晓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大四的学生。当地时间3月14日,学校正式停课。但在之前,蔡晓去上课时就注意到,身边不少中国同学都在讨论如何买机票回国。“三月初,温哥华直飞国内的机票就已经很紧张了,到了三月中旬,回国航班基本已经卖光了。”
为了避免长途飞行中的交叉感染,蔡晓戴上了口罩。等她到了机场发现,不少回国的留学生全副武装,不仅戴多层口罩,还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而在温哥华机场,防控疫情的气氛已经趋于紧张。在值机的服务台处需要测量体温,而在安检前还需要测量一次。“登机时又测了一遍,路上测了一遍,下飞机又测了一遍,反反复复很多次。”
温哥华到厦门需要飞行12个小时。蔡晓发现,以往飞机餐的餐盘变成了一个外卖盒,里面有能量棒、巧克力、水果罐头等已被密封的食物,除了热水,其他饮料都改为密封包装。但12个小时的航程中,很少有乘客吃东西或喝水。大家无人摘下口罩,也鲜有人互相交谈。
蔡晓注意到,乘务员戴着双层橡胶手套和口罩,每个卫生间前都有乘务员值守。蔡晓去卫生间前乘务员递给她一双手套,并要求她戴上,出来后又指导她把用过的手套扔到一个指定的袋子里,并给她的双手消毒,“使劲儿让我擦手”。
飞机落地后,机组通知所有人员不要走动,等待检疫人员上机检查。“检疫人员给从美国回来的人单独贴了标签,让他们先下机。之后机上广播要求旅客以每三排为单位下机。”
蔡晓在飞机上填写了健康申报表,下飞机入海关,共有三批工作人员帮她检查。“帮我检查表填的对不对,有没有填好。海关那里的自动测温装置也能监控我们的体温。”而在国内航段,蔡晓一上机就收到了乘务员发放的消毒湿巾和手套。飞机落地后,机场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境外归国人员申报点帮助蔡晓申报。
目前蔡晓正在济南市的集中隔离点,即将结束隔离。她已经通过了核酸检测,每天需要报备三次体温。“这半个月觉得很温馨,从航班到隔离点,工作人员的工作实在是太细心了。”
“盼着回家,盼着重返‘自由’。”从隔离酒店的窗户向外望,北京街上渐渐有了春的生机。此时,悉尼大学毕业生袁林正在北京海淀区一家酒店进行隔离,如果没有疫情的发生,他原本计划在三月底续签工作签证,继续在悉尼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
疫情的发生加速着袁林的回国计划。3月初,他购买了从悉尼回国的机票,“留在这里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工作辞了,签证也不续签了,以后在家乡找工作吧。”
袁林回忆,返回中国的飞机上,座位几乎被坐满。“大多数乘客是中国人,都知道疫情有多严重,所以大家也都很谨慎,全程除了吃饭,不会摘下口罩,就怕有传染风险。”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袁林产生了久违的安全感。“首都机场的体温检测很严格,入境管理也很严格,我一下飞机就被带去隔离酒店了,除了乘客和穿着防护服的管理人员外,这些天我没再见过其他人。”
回国之前,袁林在悉尼拍摄了一些视频素材。这些天,袁林经常通过剪视频的方式度过隔离期间无聊的日子,他也经常回忆起在澳洲求学的时光。“恍若隔世。”

蔡晓在集中隔离点的饭菜。 受访者供图
疫情之下:很难在当地人脸上看到焦虑
让袁林选择回国的原因之一——当地人对疫情的态度。
“面对疫情,我觉得澳洲人是恐慌的,澳洲刚开始有新冠肺炎病例时,我在这边就已经买不到口罩了,卷纸也买着很困难。”但当地人对聚会的热情又让袁林感到不解。
回国前,想到短期内不会重返澳大利亚,袁林戴上口罩,去悉尼歌剧院、邦迪海滩等地,拍摄了大量视频素材,渴望以此铭记这两年在悉尼的留学时光。让他意外的是,“歌剧院边上的草坪,酒吧里,都有大量聚会的人,他们不害怕吗?”
拍摄素材期间,袁林也经受了来自旁观者的非议。“有一次,我在桥边拍摄的时候,一个经过的司机看我戴着口罩,摇下了车窗,对我喊了一句‘Virus’(病毒),又摇上车窗开走了。”这些场景让袁林产生了一种剥离感,“也许回国会更好过一些。”
疫情之下,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硕士生陈思选择留在德国,3月25日是他本学期最后一门考试,但是随着学校停课,考试也随之取消。他把外出次数减少为7-8天一次,每次外出采购一些水果、蔬菜和日用品,矿泉水等较重的日用品则通过网络购买。
斯图加特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首府和第一大城市。陈思告诉记者,巴登-符腾堡州已经成为德国疫情第二严重的州,有超过4000例确诊病例,其中斯图加特有100多例。但在斯图加特的街上,却很难看得出人们因疫情而焦虑。陈思住所附近的街区也似乎和往日没有什么两样,“很多德国家庭还是在室外散步、玩,和疫情前的状态很类似”。
疫情期间,陈思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不少其他国家超市中厕纸、水被一抢而空的图片。但在斯图加特,当地超市中的水果、蔬菜、肉类以及包括厕纸在内的日用品供应相对充足,唯一短缺的商品是面粉。“可能大家囤了面粉做面包,但面包还能买到,不过口罩已经买不到了。”
此外,疫情的影响在一些细节上还是得以体现。陈思坐地铁去超市采购时发现,以往满满当当的地铁车厢如今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而在斯图加特市中心,街道上的人流量也明显减少。
实际上,斯图加特当地人对疫情的态度直到近两周才开始紧张起来。3月初时,仍然有德国同学与陈思开玩笑,说亚洲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欧洲人可以不用害怕,“我觉得匪夷所思,但他们还让我放松些,说是科学家说的。”
3月8日,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曾建议取消一千人以上的群体活动。但令陈思哭笑不得的是,一些一千人以上的音乐会观众人数被组织者削减至999人,音乐会仍按期进行。3月9日,斯图加特还举办了一场和比勒菲尔德的德甲比赛。官方只是敦促球迷注意预防措施和卫生规则。
陈思是一名摄影发烧友,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经常能看见他用相机记录下的德国街头。从3月20日起,斯图加特政府建议市民无故不要出门。陈思告诉记者,实际上如果拿相机去拍照被发现会被罚款。“以前很喜欢走街串巷搞街头摄影,现在只能偷偷去楼下的小树林拍拍风景了。”
陈思最担心的是,斯图加特大学对于校园内确诊病例的披露并不及时。“上周学校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被确认,但学校四天之后才在官网发布了消息。”陈思未雨绸缪,专门去了解一旦感染新冠肺炎需要如何就医。他告诉记者,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开通了24小时咨询热线,留学生、华人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了解自己的症状是否可能是新冠肺炎。“如果真的出现了症状,我们第一选择肯定是打给大使馆,因为是中文服务,不用担心语言的障碍。”
除了大使馆的咨询热线,德国当地民众还可以预约家庭医生进行初步的检查来判断自己是否感染。陈思告诉记者,即使要进行咽拭子取样,他们可以去指定地点通过一个窗口由家庭医生完成检测采样,“就像外卖窗口一样,全程无接触。”
“周围的人怎么一点都不急呢?”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读的硕士生杨静也有相似的困惑。
1月底,已有新冠肺炎病例在新加坡出现。“我看到超市里有人在排队买口罩,口罩都被抢空了,但是很奇怪,街上都很少见到有人戴口罩,戴口罩的都是中国人。”杨静说,当地人对待新冠疫情的态度是“割裂”的,一方面大家会去超市里抢购口罩、卫生纸等物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新冠肺炎疫情很少成为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
“疫情蔓延到全球后,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学校纷纷宣布取消面授课堂,3月中旬,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已出现两名新冠肺炎感染者,但我们迟迟不停课。”杨静看到,她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依然在坚持面授课程,防护措施也没有她期待中那样完善。“学校只取消了50人以上的面授课程,我所在的班级有40余人,全部的课程、考试都在照常进行,我的室友是学电气专业的,他们还在照常做实验。”杨静说,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室门口,张贴了二维码,学生在在进入教室前可以扫描二维码,填写表格记录个人信息,以便追踪潜在接触者。但“是否填写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我有事着急上课,就会忘了填。”
临近期末,杨静又多了一重心理压力。“在家实在学不进去,白天我通常会去学校的图书馆学习,到了期末,图书馆里的学生更多了,而且大家经常挤在一张桌子上学习。”杨静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学习时,对面一位亚裔同学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但没有人觉得异常,反而是杨静戴着口罩行走在图书馆时,周围的人会自觉远离她,有时还会投来鄙夷的目光。“他们觉得,只有患者才会戴口罩。”
“我们学校在新加坡的郊区,从图书馆的楼顶上看,能看到柔佛海峡。”3月17日,杨静看到新加坡邻国马来西亚宣布封国的消息,她又陷入了紧张情绪,去超市买了米、面、肉制品、鸡蛋和蔬菜,又买来了洗手液和卷纸,以防万一。
疫情之下,杨静在新加坡的日子还能照常过,只是会在上下学的路上避免人群聚集的地方。前几天,她收到学校发来的邮件,南洋理工大学终于要全面进行网络授课了,但考试形式将维持不变。“我们学校已经出现9例新冠肺炎患者了,他们怎么就不着急呢?”杨静哭笑不得。

受疫情影响,原本热衷街头摄影的陈思只能偷偷到住处楼下的小树林里拍风景。 受访者供图
相隔千里的牵挂
“新冠疫情,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留学生打全场。”虽然这只是一句对留学生的调侃,却有留学生表示,“打全场”几乎是他们的真实状态。
“有时候,相比于在千里之外担心家人,我宁愿自己处在一个较为危险的地方,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中国疫情严重的那些天,杨静几乎每次看新闻都会哭,担心家人感染。她几次情绪崩溃,给家里打电话的频率是平时的三、四倍,反复叮嘱家人不要出门,不要聚集,戴好口罩。还通过网络捐款的形式,为中国抗疫出了一份力。
看到中国的疫情有好转,杨静紧张的心情开始有所放松。转眼再看看自己所在的新加坡,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以每天十几例、几十例的速度增长着,又变成了家人不停给她打来电话,叮嘱她戴好口罩,减少出门次数。
袁林的爱人家在湖北宜昌,澳大利亚疫情暴发前,袁林和爱人每天都盯着疫情滚动数据。“看着国内增长数字,心都碎了。”
朱赫收到了来自母校的关怀。3月20日,他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国际处的通知,学校将为在海外交换的学生寄出一批口罩。
中国疫情发生时,邱邱和她的同学在纽约想方设法为国内的同胞寄送口罩。“我们联系了纽约很多厂家,对接国内负责接收、发放这批口罩的人员,饱经周折,才把口罩寄送回国内。”而今,却是邱邱的妈妈想方设法从国内为身在纽约的秋秋寄送口罩、防护服等物品。“这种感觉挺神奇的,疫情之下,人类命运紧紧相连,亲情的定义也更加丰富。”
3月22日,纽约宣布封城。从住处的阳台向外望,纽约昔日繁华的街道上已不见人影,邱邱将在这里度过一个充满未知的“长假”。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林伶、朱赫、邱邱、蔡晓、袁林、陈思、杨静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樊朔 戚望 编辑 潘灿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