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翁达杰
“小说是一个大口袋,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只要你找到某一种方式把它们架构起来。”在与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的对话中,迈克尔·翁达杰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在创作中注重文体实验的注解。尽管,他声称自己从未打算做一个实验作家、或过度专注于小说文体。说他的写作过于激进,则是因为当下的小说看似前卫,其实依然非常保守。“既然二十世纪的绘画与音乐都经历了种种激进的变革运动,小说又有什么理由仍停留在相较固定的形式?”
正如他自己所想,作为在诗歌与小说领域,都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翁达杰最大限度地对传统进行了反叛和颠覆。在小说中,他打破了与其他文学体裁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其中;他同时还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呈现给读者一种“非小说”的文学图景。而这似乎恰好印证了他复杂的血统。
翁达杰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一个富裕农场主家庭,他的身上流着荷兰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等多个民族的血液。他在父亲的大茶园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1岁时,他跟随母亲来到英国伦敦,在那里读了小学和中学;1962年,他从英国来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就读并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主要在多伦多一所大学教授英语文学。
如此,翁达杰作为跨文化和跨国界的“无国界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写作一种“世界小说”,便是理所当然。他“跨文体”的写作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的机构只是粗略地将他的作品分成“散文”与“诗歌”两类;不同的文学史家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于“回忆录”和“小说”门下。他独特的写作实践,同样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挑战,有意思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作品的畅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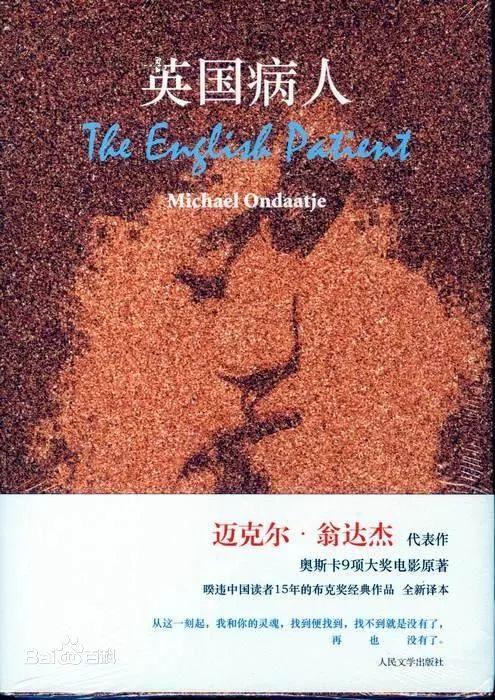
《英国病人》封面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英国病人》让他获得该年度布克奖,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更是包揽了1996年奥斯卡的9项大奖。时隔26年,2018 年,该小说获颁“半个世纪以来布克奖最佳作品”。在7月8日于伦敦南岸举行的布克奖50周年纪念特别活动——“金布克奖”的颁奖典礼上,翁达杰坦言,自己写完这部小说后就再也没有重读过。“我一刻都不相信这是最好的作品,尤其是参与角逐的有奈保尔这样的大师,或《狼厅》这样的杰作。”
某种意义上,这是翁达杰的谦辞。虽然他极富独创性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引来一些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他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域。也因为此,有评论认为,翁达杰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堪与翁贝托·埃科等后现代派小说大师并肩的重要地位。
据说,翁达杰喜欢使用笔记本写作。他通常会手写完成最初三四稿,有时还用剪刀和胶带,对段落、甚至整个章节剪剪贴贴。他的有些笔记本,里页叠着四层稿纸。对于他来说,写作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他要做的工作主要就是整理和重写语句,因此他简直没法理解文思堵塞是为何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如何不同凡响,这种癖好,却关联着他独出机杼的写作手法。翁达杰总能以一种饱含激情和诗意的笔触,用一种文化杂汇的微妙组合,将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
出版了两部诗集后,翁达杰开始了小说和其他文体的实验。1970年,他出版了一本跨文体的作品《小子比利作品选集》,假托美国历史上出现的草莽英雄、左撇子枪手小子比利的作品集的名义,运用多层结构和后现代的拼贴手法,把历史传说、作家想象杂糅在一起,探讨了美国梦的暴力特征。六年后,他推出长篇处女作《劫后余生》,小说以爵士乐先锋、吹奏短号的查尔斯·巴迪·博尔登为主人公,他嗜酒成性,与两个女人有瓜葛,被死亡的噩梦所困扰,以致31岁时发疯。从零零落落的事实中,翁达杰重构了这位爵士乐殉难者起伏跌宕的一生。



《劫后余生》《世代相传》《身着狮皮》封面书影
更激进的文体创新,则始于1982年发表的《世代相传》。在这部追述自己在故乡斯里兰卡成长过程的回忆录里,翁达杰一反传统小说的线性模式,将时间、地点、章节结构统统打乱,重新编排,并僭越文体界限,以民谣、诗歌、照片、地图、采访记录、录音材料、档案等夹杂其中。文体革新,为这部小说赢得了“后现代编史元小说”的名声。五年后,翁达杰出版了《身着狮皮》,书名取自于古代巴比伦的神话传说史诗《吉尔伽美什》,说的是英雄吉尔伽美什在朋友死去之后,独自披上狮子皮浪迹于荒野之中。在这部小说里,翁达杰首次真正触及加拿大题材。移民后裔帕特里克·刘易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加拿大偏僻林区来到多伦多,在这个跃动、混杂的城市里,他靠搜索一位失踪的百万富翁和挖掘安大略湖底隧道谋生。在此过程中,他先后爱上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位是富翁的情妇,另一位则是她的闺中密友。帕特里克生命中的这两个女人都有着最奇特的神秘特质,让他痴迷,赋予他力量,使他平凡的人生发生了巨大改变。这部小说为翁达杰赢得了“立体主义”小说家的声誉。

电影《英国病人》剧照
在此后的《英国病人》中,翁达杰的小说艺术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呈现。“金布克奖”评审之一、斯里兰卡裔英国小说家卡米拉·山姆西评价说,很少一本小说像《英国病人》这样,它就像是进到你的皮肤里,而且不断地让你去重读,还总给你新的惊喜和收获。“这部作品在史诗感和亲密感之间无缝衔接,这一刻你看到的是无垠荒漠,下一刻你看到一个护士把一片李子放进病人的嘴。语言精巧,结构漂亮,每一页都渗透着人文主义气息”。
如其所言,小说以一种优美而抒情的笔调,营造了一个在二战末期,已渐渐远离战争的弥漫着朦胧诗意的“心灵田园”。生活在这如画“田园”中的四个人,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背景。加拿大籍哈娜的生父、继父与生母皆为了建设英国殖民地而受伤致死;卡拉瓦吉欧为英国做谍报工作而被德军截断双手;印度锡克教徒基普内心极度痛恨英国殖民主义;来历不明的“英国病人”奥尔马西伯爵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烧伤。小说紧扣殖民主义和战争暴力下的精神创伤,试图通过跨民族、跨文化、跨历史的“超越性理解”,寻求“灵魂之伤”和“生命之缺”的治疗与救赎。
事实上,翁达杰笔下的主角,无论年龄、性别,大多抹去了国籍与身份,流浪他乡。比如,他的小说《猫桌》写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十一岁的男孩从科伦坡乘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他被安排坐在了离船长及达官贵人们最远的“猫桌”上——跟一群“无足轻重”的成人和两个男孩坐在一起。轮船横渡印度洋,跨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甲板的自由空气中,男孩们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冒险。同时也有其他的事物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一个男人跟他们聊爵士与女人;一个男人为他们打开了文学世界的大门;男孩美丽又难以捉摸的表姐艾米丽成为了他的知己,第一次让他“保持一定距离”地审视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欲望;还有一个每天晚上出来放风的犯人,让这趟旅程变得神秘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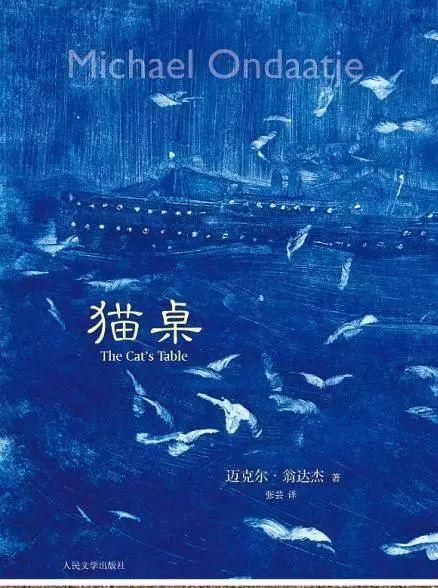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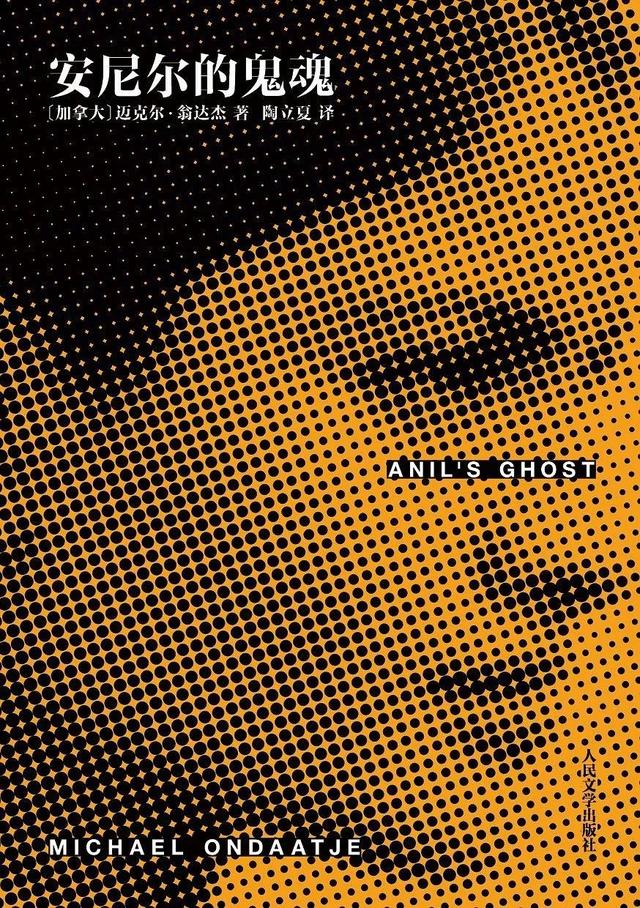
《猫桌》《安尼尔的鬼魂》书影
然而,翁达杰出版于2000年的《安尼尔的鬼魂》,就像小说译者陶立夏所说,却是写的是回归与坚守,法医安尼尔受国际人权组织派遣,回到祖国斯里兰卡调查因内战而愈演愈烈的人口失踪案。此时的科伦坡被恐怖与悲伤笼罩,政府自负虚荣,“每种政治观点都有它自己的军队撑腰”,市民无故失踪,不计其数的尸体被焚烧、藏匿和掩埋。随着无名尸骸身份的确证,屠杀的丑行暴露于天光之下:一个挖掘黑暗的故事。或许,每个人心里都存在着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世界,他们默默地构想着自己的拯救之途。拯救的意愿把他们紧紧连接起来,而不同的方向却让他们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如果说,在翁达杰的这四部长篇里还能依稀勾画出故事情节的完整面貌,在《遥望》中,这种勾画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误读。小说书名“DIVISADERO”来自西班牙语,有两重涵义,其一为“分隔、分离”,其二为“远观、遥望”。正如书名所预示的那样,小说奇怪地“分裂”成两个部分,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只能说,这两个部分是互相“遥望”的。

《遥望》封面书影,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农场,父亲和女儿安娜,养女克莱尔和养子库珀生活在一起,生活平静,但正在长大的孩子们内心波涛涌动。十六岁的安娜和库珀之间的私情被父亲发现,安娜出走,成了一个文学研究者,到法国乡村研究已故作家塞古拉的生平,库珀成了一个赌场牌手,克莱尔成了一个公设辩护律师的助手。多年后,克莱尔遇到了库珀,但库珀很快就因遭受殴打而丧失了记忆。而安娜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她在法国遇到了一个叫拉斐尔的吉他手……
就如支离破碎的情节所呈现的那样,小说的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块状的,像是几个完全不同色系的色块,被并置于画布之上,互相之间或有重叠,或有冲撞与呼应,它们之间并没有时间的逻辑关系,就像一部时空交叉的电影,读者唯有依靠自己的想象和敏悟,才得以建立一种可能的“整体”。
然而,如同翁达杰的其他作品,《遥望》中复杂错乱的创作艺术,并没有淹没他敏感的心灵。小说里尼采的箴言重复响起:“有了艺术,我们才不会被真实的残酷所毁灭。”很显然,翁达杰的创作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样本。相反,它以艺术抵抗真实的残酷,以诗意慰藉创痛的心灵,正因为此,他的诗意与关切才如此震撼人心。

译作选读

节选自
《战时灯火》
[加]迈克尔·翁达杰/著
吴刚/译
读客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11月版
导读
1945年,14岁少年纳撒尼尔的父母走了,把他和姐姐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
外号“蛾子”的人终日行踪不定,“镖手”的身份似乎也并不简单。他们还带来了一群陌生人,每个人似乎都身怀秘密,似乎都与少年的母亲有着某种关系。
十多年后,31岁的纳撒尼尔还对母亲当年的突然离弃耿耿于怀。他决心挖掘无法理解的往事,试图拼凑出当年完整的故事……
01
1945年,我们的父母走了,把我们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条名叫卢维涅花园的街上。一天早上,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提议全家人早饭后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告诉我俩他们要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上一年。算不得太长,他们说,可也不是一趟短暂的旅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记得父亲道出这个消息时,坐在某一把那种不太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母亲则穿着夏天的裙子站在他背后,看我们作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抓过姐姐蕾切尔的手来抵在腰上,仿佛能给它带来温暖。
我和蕾切尔都没有作声。我们望着父亲,他正在跟我们详述这趟行程的细节,他们要乘的是新式阿弗罗都铎I型飞机,是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后裔,巡航速度每小时可以超过三百英里。在到达目的地前,他们必须至少转两次机。他解释说,他升职了,要去接管联合利华设在亚洲的办事处,这对他的事业来说是更上层楼,会给全家人都带来好处。他说得很严肃,母亲听着听着侧过身子去看她那八月的花园了。父亲讲完后,母亲看我一脸迷茫,就来到我身边,用手指梳弄我的头发。
我当时十四岁,蕾切尔快十六了,他们跟我们说,假期里会有一个监护人来照顾我们,母亲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说那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事。我们已经见过他了——我们一直都管他叫“蛾子”,这名字是我们给起的。我们家里都有起外号的习惯,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有伪装的家庭。蕾切尔早就告诉过我,她怀疑那人的身份是罪犯。
02
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奇怪,但在战后那段时期,生活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有点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我们接受了这个决定,是孩子都会接受的,也接受了由“蛾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他最近成为了我家三楼的房客,是个低调的人,个子虽然大,但举手投足都带着羞怯,还真有点像蛾子。爸妈肯定认为他是可靠的,至于他们看没看出来蛾子是罪犯,我们说不太准。我猜想,曾经家里也有人努力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其乐融融。父亲隔三岔五会叫我陪他去联合利华的办公室,周末和银行休假日那里通常都没人。
他在那儿忙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栋大楼的十二层瞎逛,宛如置身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我发现,所有办公室抽屉都是锁着的,废纸篓里空空如也,墙上没有画,不过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倒是有一幅大大的立体地图,标出了公司在海外设的点:蒙巴萨、可可群岛、印度尼西亚。离本土稍近点的有的里雅斯特、赫利奥波利斯、班加西、亚历山大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我想那些地方都是归父亲管的。他们就在这里掌控着数以百计的船只往来于英国和东方。地图上标出那些城市和港口的小灯珠在周末关着,跟那些遥远的贸易前哨站一样隐没在黑暗中。
到了最后关头,爸妈作出决定,母亲会在夏天的最后几周里留下来,把房客照顾我们的事安排停当,帮我们做好上新寄宿学校的一应准备。父亲孤身飞往那个遥远世界前的星期六,我又一次陪他去了趟位于柯曾街附近的办公室。他建议我们好好走上一段,因为,他说,在接下来几天里他的身体都将会窝在飞机上伸展不得。于是我们搭公共汽车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一路走着穿过海德公园直抵梅费尔。那天父亲显得不同寻常地兴致高昂,边走边唱着“家纺的衣领恋家的心,走遍天涯难舍故园情”,唱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洋洋自得的地步,仿佛这是一条天经地义的道理。这歌词什么意思呢?我不很明白。记得进入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需要几道钥匙,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占据了那栋楼的整个顶层。我站在那幅灯珠依然没打开的大地图前,努力记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会飞经的城市。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地图。他来到我身后,打开了灯珠,立体地图上的山脉霎时投下了阴影,不过这时我不太注意那些灯珠了,我更注意的是被淡蓝色灯光照亮的港口,和大片没有被照亮的陆地。这已经不再是一幅能一目了然的景象了,我怀疑蕾切尔和我看待父母婚姻的眼光一定与此相仿,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他们很少跟我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我们习惯了片面的故事。父亲一直沉浸在稍早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我认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和我们是一路人。
说到他们的离开,大家已经接受了,母亲必须要跟他一起走:她不可能,我们是这么想的,离开了父亲而存在——她是他妻子。与母亲留在卢维涅花园照顾我们相比,把我们留下会对整个家庭少造成一点伤害,会减少一点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可能。据他们的解释,我们俩的学校都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不能这么一下子说离开就离开。父亲离开前,我们全都和他拥抱,四个人抱作一堆。蛾子在那个周末很知趣地消失了。
03
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一时还有点难以置信。我依然难以确定,接下来的日子会毁了我的生活,还是会令它充满活力。这段日子里我会摆脱家庭习惯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但随后,作为结果,我会在行事上变得犹豫不决,就仿佛我已经太快地耗光了自由。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到了能谈论此事的年纪,谈谈我们怎样在陌生人的臂膀保护下成长。这有点像是在弄明白一个童话寓言的含义,这个童话寓言关于我们的父母,关于蕾切尔和我自己,关于蛾子,也关于后来加入我们生活的其他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都有固定的套路。某人接到一项考验,要他去完成。没人知道谁掌握着真相。人们既不是我们所想的身份,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认为他们该出现的地方。还有一个人会在不知道的某处旁观一切。我记得母亲很喜欢讲亚瑟王传奇里交给忠勇骑士们的那些令人心情复杂的任务,记得她是怎么跟我们讲那些故事的,这些故事有时候会把场景设定在巴尔干半岛或意大利某个有名有姓的小村子,她声称自己到过那里,还会替我们在地图上找出来。
(《战时灯火》[加]迈克尔·翁达杰/著,吴刚/译,读客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