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5月7日,新加坡S11榜鹅客工宿舍确诊病例达2526例(图/Getty Images)
4月上旬以来,新加坡已有39个外籍劳工(又称“客工”)集体宿舍爆发群聚感染。截至5月7日,新加坡累计确诊的20939例确诊患者中,有18483例是住在集体宿舍的客工,占确诊人数的88%。
“这仍然是马拉松的上半场。”近日,新加坡政府疫情应对工作组组长黄循财在回应媒体采访时称,虽然几周内新加坡确诊病例从数百增至两万,但该国的疫情尚未过半。
目前,新加坡约有百万余名外籍劳工,中国在新加坡务工人员约7万名,主要从事建筑、制造、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受当地新一轮疫情爆发的影响,不少中国劳工仍隔离在外籍劳工集体宿舍中。

确诊后的刘志康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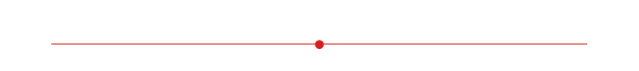
确诊于客工宿舍
在新加坡5月7日新增的741例新冠确诊病例中,绝大多数是住在集体宿舍的外籍劳工,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仅占5名。
新加坡政府疫情应对工作组组长黄循财5月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随着对客工宿舍进行“广泛的测试”,新加坡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现大量的新病例。
在“广泛的测试”中,中国劳工刘志康确诊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感染上新冠病毒的。也许是在客工宿舍的一楼大厅,那里在饭点时会聚集上百人;或者是在隔离区,没有人知道那里的室友们是否已经受到感染。
刘志康今年48岁,在新加坡做建筑工人,装修、刷漆等是他的日常工作。疫情发生前,他住在新加坡克兰芝客工宿舍。4月21日,新加坡政府宣布住在客工宿舍的所有客工不论所属领域一律暂停工作。他的宿舍开始了隔离封锁。“劳工们被限制了出行,如果有人不服从安排,想要离开,就会被扣下‘工作签证’,彻底失去这份工作。”刘志康说。
4月25日,刘志康感觉自己肌肉酸痛,有些头晕,体温38.3摄氏度。医生带他去做核酸检测,“他把一个塑料的小条子,放进我鼻子里,又拿出来,几秒就结束了”。接着,刘志康被带离宿舍,转移到客工宿舍的“隔离区”。
“隔离区”并不意味着“单独隔离”,它的构造和宿舍相似,一层楼有26个房间,每个房间有12张床。4月26日,刘志康进入“隔离区”时,宿舍里已经住了3个人,“最少时我们这间住过2个人,最多时住过8、9个人”。刘志康从医生那里了解到,住进隔离区的人都是因为出现过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
他担心自己住在这里反而会被感染,连睡觉也不敢摘口罩,“我戴两层口罩睡觉,但现在看来,好像用处不大”。医护人员告诉他,只要隔离14天没有问题,就可以回去了。
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5月2日下午,刘志康确诊,他被带离隔离区,入院接受治疗。刘志康的病房里有8张床位,在他住院时,病房里已经有了5位中国人和2位孟加拉人,都是轻症患者。目前,其中三位已经康复出院。
入院5天后,刘志康感觉自己咳嗽、发烧的症状好转。每天早上10点,护士会组织病人们做“广播体操”,还会带他们做小游戏——在远处放一个筐,向里面投球,投中多的人会被奖励一瓶汽水。除了有时感到伙食有点不够吃之外,他很满意医院的生活,“比在劳工营里好得多了”。
截至5月7日,刘志康曾住的克兰芝客工宿舍已累计确诊410人。
在医院里治疗的刘志康每天都会和家人打电话报平安。5年前,他来到新加坡工作,今年1月初回安徽老家过完春节后,原本订了2月11日去新加坡的机票,但临行前几天被取消,他改签到2月6日提前回了新加坡。
现在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和雇主的劳动合同将在6月6日到期,“不知道到时候能否顺利回国”?

5月2日,何昊所在宿舍的全体人员被叫去做鼻拭子检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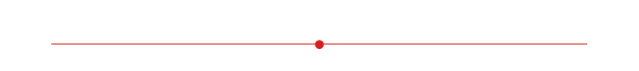
“1个人感染,11个人都要遭殃”
5月2日,何昊从新闻中了解到,他所住的客工宿舍楼确诊了17个新冠肺炎病例。但他无从得知确诊客工具体住在哪个宿舍,“心里特别没底”。当天,他被安排了核酸检测,目前暂未拿到结果,仍住在客工宿舍中。
何昊所在的宿舍楼位于新加坡大士1道16号,名叫JTC Space,平日里面住着大约400名客工,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国人。这家新建的宿舍有大面积的绿地,以及专供客工消遣的电视室、阅览室、健身房、足球场等公共设施。
何昊的宿舍有100多平米,由一个大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两个浴室、三个卫生间组成,住11个人。何昊觉得住的还算舒适,“和在学校里差不多,当然我们的宿舍新,其他劳工宿舍就不像这样了。”
“现在宿舍楼里人少了,很多人提前被雇主接出去了”。何昊说,4月中旬,疫情在客工宿舍爆发时,一些公司把员工接出去安排在宾馆里隔离。何昊的同事也曾向人事部反映过想搬出去住,但还未得到批准。何昊也有些担心,“毕竟这里人多,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感染”。
何昊无法和室友们保持社交距离,11张床挨得很近,他认为,只要宿舍里有1个人感染,11个人都要遭殃。
“我们4月22日之前全部都还在上班,那时新加坡感染病例已经很多了”,4月21日晚,何昊接到人事处电话,让他上完当天的晚班后,转天开始“休息”。
在宿舍隔离的时间里,何昊不希望白白浪费,他报了一个线上英语培训班,上午学习英语背单词,下午锻炼身体,晚上和家人视频聊天。
30岁的何昊在新加坡一家数控机床加工厂做技术工。2012年,他从技术专科学校毕业,通过劳务中介来到新加坡做工,经过8年的努力,底薪从4000元涨到8500元人民币,算上加班费,每月能挣到约18000元人民币。“中国工人都会选择加班,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何昊说。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何昊原本打算在今年春节离开新加坡,回江苏老家发展,与妻子和孩子团聚。1月底国内疫情开始爆发,回国航班减少,机票价格高,他想等一等再买,结果没等几天,航班就彻底取消了,他只好继续在新加坡上班,没想到又赶上了新加坡客工宿舍爆发的新疫情。
眼下,何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国,他打算等到新加坡疫情完全结束再回去,“我不想给国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闫万住的客工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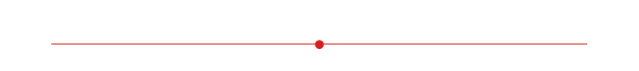
希望可以早点开工挣钱
2018年,闫万的女儿去了新加坡上大学,为了能多看看孩子,也为了多挣点钱给女儿交学费,闫万和爱人通过劳务中介,先后到新加坡做客工。去年1月,49岁的闫万开始在新加坡一家连锁餐厅做厨师。
为了方便上班,闫万住进了离餐厅很近的本茱鲁径的Cassia@Penjuru客工宿舍。他感到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雇主的员工少,房间里一共5个人住,包括他和其他4名孟加拉人。闫万说,“像是船厂或者建筑公司,他们有的宿舍有12到20人”。
闫万所住的客工宿舍区有十多栋楼,住着五六千人,大多是孟加拉和印度人。隔离时期,每天有新加坡政府的工作人员送一日三餐到宿舍大门口。
午饭时间里闫万能到院子里“透透气”,但通常在楼下呆个十来分钟就要上去了。
隔离初期,公司给每个客工发了一个可以反复洗的布口罩,“有点像国内那种劳保口罩”。和母亲在外租房住的女儿听说后很担心,专门来给他送了盒一次性医用口罩。
闫万没有询问雇主关于停工期间薪水的问题,他从新闻中得知,“政府要求新加坡的雇主给客工正常发工资”。4月11日,新加坡人力部发表文告称,在阻断措施推行期间,住在宿舍的客工行动会受到限制,雇主仍要通过财路转账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来向客工支付薪水。但闫万估计老板可能不会给全薪,“政府给公司的补助金应该还是会发的,可能每个人算起来也就是八九百块钱新币(约合人民币4000元)。”
除了补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表示,政府目前正在为客工进行大范围的病毒检测。
4月28日,闫万的一个孟加拉室友被叫去做新冠病毒检测。一天后,室友的检测结果出来,呈阳性。
因为语言不通,闫万和4名孟加拉室友的交流不多,他不是很担心自己受到感染。“是一个宿舍的,但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说话,床也不挨在一起,避免了飞沫传播。”闫万介绍,宿舍里三面都有窗户,全部打开,风扇也24小时不停地吹,他没有感到身体不适,打算等几天看老板有什么指示再说。
5月7日早上,闫万和另外三名室友也被安排做了核酸检测,目前还在等待结果。
“我已经失去自由20天。”闫万说,他希望可以早点开工挣钱。截至5月7日,闫万所在的Cassia@Penjuru客工宿舍已累计确诊123人。
对于疫情在客工宿舍的爆发,闫万有着自己的看法,“除了一个房间住12个甚至更多的客工无法保持安全距离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疫情爆发之初,忽视了客工宿舍的公共卫生管理。”
据《联合早报》4月18日报道,自2月初发现第一例客工感染病毒后,有不少其他客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相继感染。有质疑声音认为,两个月的时间内,由于针对客工宿舍的防疫和检测措施不足,使其成为新加坡疫情反弹的最大防控漏洞。
5月4日,新加坡官委议员在国会提到客工宿舍里的生活情况,特别是现在为了确保新加坡人的安全,使客工们处在“全面封锁“的状态下,并问政府会否考虑向客工们道歉。当日的部长声明称,“我们将检讨如何提高标准,并留意那些可能尚未达标的旧宿舍。”

陈启明住的12人劳工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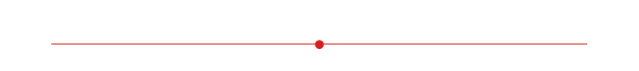
“还要被隔离多久?”
隔离在客工宿舍的日子里,陈启明时常想不起来“今天是几月几号”。
半个多月来,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同另外11个舍友一起挤在30平米的宿舍里吃饭、睡觉,躺在床上玩手机或看电影。他住在上铺,下床后也没有多少可以活动的空间,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床上度过,“浑身疼”。
陈启明在新加坡一家制造厂做工,他住的客工宿舍楼位于新加坡西海岸,共有7层,其中有6层用作客工宿舍,每层分有6个宿舍,1个卫生间和1个公共澡堂,每个宿舍有12个床位。
4月7日,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关停工作场所和学校等一系列代号为“断路器”的措施。彼时的陈启明还在工厂干活,因怕被感染,他从客工宿舍搬去工厂里住,一个房间只有他和另一个中国人,“虽然只能打地铺,但活动空间大”。
18日晚上11点,陈启明接到了经理的电话,要求“马上搬回宿舍”,但没有告知原因。那时陈启明所在的工厂还没有确诊病例,但他听说宿舍隔壁的办公室里有人感染。
凌晨十二点回去后陈启明再也没有离开过宿舍,登记在宿舍名下的其他劳工也被要求返回进行集中隔离,12名客工一起挤在30多平米的空间里生活。他们被通知在宿舍里“自主隔离”,“自己管自己”,公司每天会有管理人员来登记体温,清点人数。陈启明不敢离开宿舍,他一方面担心私自离开可能会丢掉工作,另一方面觉得“就算现在出去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宿舍里除了4个中国人外,其余都是印度人,语言、作息、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让隔离在一起的客工们时常出现一些摩擦。有时,陈启明甚至觉得宿舍“像监狱一样”。
陈启明最害怕客工宿舍的密闭空间里发生聚集性感染。新加坡常年温度在30度上下,气候潮湿,为了保证室内在疫情期间的通风,他们不得不打开窗户,逼仄闷热的环境令他坐立难安。
担心被感染的日子里,陈启明能做的只是每天反复给自己测量体温。除此之外,他和室友们还增加了清洁宿舍的频率——从每周3次变为每天3次。
隔离期间,伙食费要自己出,为了省钱,陈启明每天会“故意晚起”,一天只吃中午和晚上两顿饭。他只点一家饭店的饭菜,因为“便宜,也会送过来”。送饭的人一般把盒饭放在宿舍楼下,下楼取餐是他一天中仅有的“放风”时刻,但不能逗留太久,否则会被举报。
饭菜多数时候是豆芽、土豆、茄子,也有些碎肉末,一天两餐需要花40元人民币。他有时候觉得自己“要吃吐了”,但又自嘲“都这时候了还要求啥”。
陈启明今年30岁,尚未成家。早年经商失败后,负债十几万,2018年来到新加坡打工。疫情前,陈启明每天做喷漆、补泥、打磨、抛光的工作,只要勤快些,愿意加点班,一个月他可以拿到12000元人民币。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爆发前,陈启明觉得自己会一直在新加坡干下去,直到把债还清。但现在他动了回国的念头。
想家时,陈启明会和父母视频——他走出宿舍,坐在楼道里,视频背景是空荡荡的楼梯,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在宿舍里的处境。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4月21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称,把4月7日开始实施的代号为“断路器”的计划延期至6月1日,这意味着他至少还要再隔离近一个月。
陈启明担心,如果新加坡的疫情始终得不到缓解,客工们或许还要被隔离更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文:计巍 宋建华 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感谢授权新加坡眼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