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冬敏 林梦月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蔓延流行,将公共卫生事宜推到世界各国治理社会的前沿。疫情控制成效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命安全、日常生活、企业经济发展、工人就业和社会安定。从全球抗疫的整体效果看,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在疫情控制方面做得很出色,尤其是中国疫情控制成效突出。欧美国家疫情控制不得力,不断出现疫情反弹的危机,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接踵而来的是经济下滑、失业上涨。美国疫情尤其严重,至今已有三千三百多万人确诊,六十万人死于新冠。针对这一情况,全世界人都在反思,为什么在美国这样医疗科学技术顶尖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中国与美国之间会产生如此落差?
2021年6月5日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公共卫生的行为意识与国家发展”线上讲座,围绕此番诸多问题展开研讨。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等海内外200余名师生参与此次讲席盛宴。美国阿尔玛大学历史系主任、雷德·诺克斯讲席教授(Reid Knox Professor and Chair in American History)卜丽萍担任主讲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方小平教授担任与谈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卜丽萍教授八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1995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与政策博士学位,在美国外交政策、公共卫生、国家建设、文化交流等领域发表多部专著,代表作有《公共卫生与中国的现代化,1865-2015》《公共卫生与战后亚洲》《科学、公共卫生及现代亚洲国家》等。此次担任与谈人的方小平教授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兴趣为二十世纪中国医疗、卫生和疾病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史,出版专著包括《赤脚医生与现代医学在中国》以及《霍乱大流行与中国社会重构》,多篇论文发表在《中国季刊》《近代中国》《医学史》和《近代亚洲研究》等专业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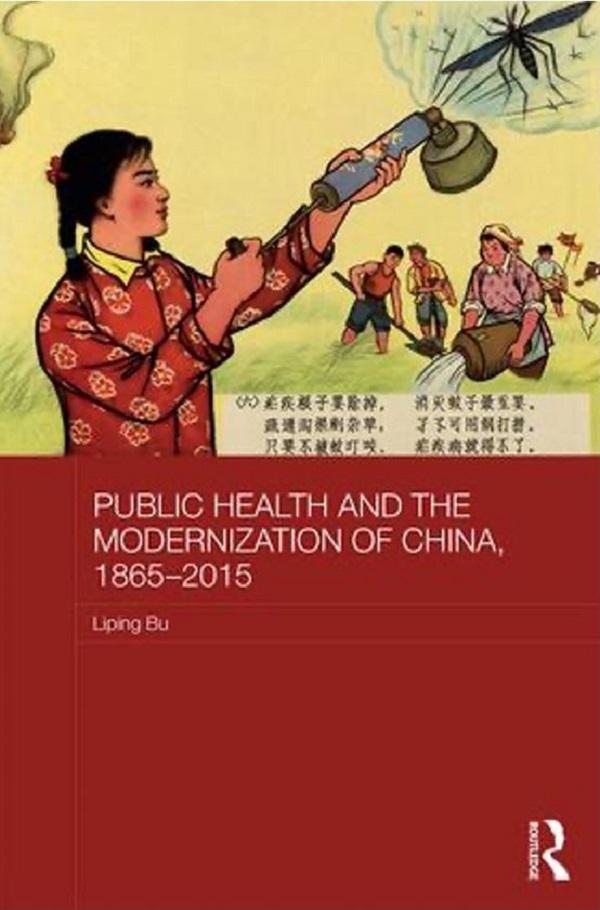
《公共卫生与中国的现代化,1865-2015》
一、城墙内外:迥然不同的新冠疫情状态
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疫情的阴影盘旋笼罩着人类,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新冠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世界各国又紧绷神经,拉响红线,出隔离防疫举措,研发推广疫苗等强硬措施,以期改变现状。此次疫情中,中方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表现出来迥然不同的态度,防疫效果也截然不同。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病毒流行的巨大差别反映了多维问题,引发了学者、公共卫生专家,医护人员以及普通民众对公共卫生行为的反思。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什么会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表现出如此负责、有态度、勇担当的公共卫生行为呢?卜丽萍教授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人民有对社会负责的公共卫生行为意识。本讲座分析探讨了中国社会形成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的历史进程。
对于新冠疫情,中美两国呈现的状态的反思,学者诸说纷纭。长期以来,美国具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发达的医疗资本、高科技的医疗设备、顶尖的医疗研究水平,是无数专家学子顶礼膜拜,心向往之的“麦加”圣地。然而,此次新冠疫情当中美国的高死亡率、高传染率,一系列的公共卫生应对举措却令人大跌眼球,专家学者对此各抒己见。或是将其归咎于民众对国家缺乏信任,或是将其归咎于国家卫生基础建设薄弱。对比中美两国,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生成的历史原因、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卫生观念的塑造过程,社会意识变迁的历史轨迹等问题,鲜有学者探究。
二、日常生活: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的形塑
何为公共卫生行为?卫生的含义是复杂的,既包括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公共卫生等多维解释。今天,公共卫生行为包括:洗手、消毒、戴口罩、保持个人和环境清洁卫生,安全等。公共卫生行为意识包括人们对卫生与疾病传染的认识,消毒、戴口罩与保持清洁的卫生行为以及预防疾病和人民健康卫生观念,个人卫生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公共卫生行为意识是基于卫生宣传教育,是中国公共卫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德的一种表现。
美国社会个人的卫生观念和中国社会的个人卫生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不同的面向。譬如,在蔬菜的日常洁净当中,美国人直接食用商场买来的蔬菜,不进行清洗,而中国人则习惯把买来的蔬菜清洗干净再用,食物中毒已然成为美国频发的公共卫生问题。戴口罩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引发了全球热议。围绕是否需要佩戴口罩的问题,美国爆发了多次游行示威,媒体竞相报道,掀起舆论风波,甚至引发了国会争论,口罩的政治化与社会环境的嬗变密切交织。在美国人看来,口罩是亚洲特有的文化“标签”。事实并不尽然,口罩进入中国实乃20世纪以后的故事,民众大规模戴口罩的行为意识也发韧于此时。回溯历史,1918年大流感爆发时期,美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大众媒体,乃至普通民众也曾大规模戴口罩,而且视为爱国行为。但这成了美国人“被遗忘的历史”,将口罩作为区别亚洲“他者”和欧美国家“我者”的身份标签,将口罩上升为东西方文化的问题而非公共卫生防疫的问题。历史上的口罩书写是如何演绎成为今日的亚洲“口罩符号”呢?
公共卫生行为意识可以解读这种变化的视角之一。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公共卫生行为意识内涵是人们对于自己所处在的社会的一种感觉,个人卫生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意义。中国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的形成发端于20世纪。长期的公共卫生教育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一起,是公共卫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行为意识表徵于社会公德。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及社会准则的强调,社会公德意识深深根植于民众的个人行为规范当中。个人的行为意识与社会公共安全、社会公共行为相联系。
三、探赜索隐:公共卫生概念的历史嬗变
20世纪,公共卫生和国家权力、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和民族复兴交织,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公共卫生状况是国家实力强弱的征徵,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卜丽萍教授近年出版的专著《公共卫生与中国现代化(1865-2015)》尝试从政治与国家权力角度阐述公共卫生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复调。全书一共由五章构成,第一章论及公共卫生和国家权力的现代概念的缘起;第二章阐述了1910年至1920年间,科学转向、民族复兴和公共卫生,第三章分析了国民时期,南京政府如何建立现代卫生系统,倡导公医制;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发动群众,倡导人民卫生运动,为爱国卫生运动奠定基础;第四章的主题是人民卫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公共卫生被纳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系中;第五章涉及经济改革体制下新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直至今日,公共卫生举措仍然处于不断变革当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公共卫生事宜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存亡。20世纪初,中国开始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机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天津后,清政府和外国列强谈判收回被占领城市。北京归还给清政府后,列强以中国没有公共卫生防疫机构为借口,迟迟不归还天津,直到清政府承诺建立防疫处后,列强才归还天津。1902年,中国第一个现代防疫处北洋防疫处在天津建立。1910年,东三省鼠疫爆发时,俄国和日本在东北都有租界,日俄等国以保护当地侨民为借口,提出扩大防疫区域,企图占据更多领地,遭到清政府拒绝。清政府任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伍连德领导抗疫,伍连德显赫的教育背景和科研实力堵住了日俄强制干预中国公共卫生的诸多理由。1911年,伍连德领导的防疫人员控制了鼠疫, 同年东三省防疫处建立,彰显国家公共卫生主权。东北鼠疫期间,伍连德利用严格的封锁、隔离、消毒、火化等等方式控制疫情蔓延。他果断推断出瘟疫通过空气传播,提倡戴口罩,这也是“伍氏口罩”的由来。彼时,参与抗疫的西方传教士医生及专业医护人员并不认同伍氏的这一做法,死伤惨重。而后汲取教训,口罩也就此盛行开来。美国医学史著名学者罗芙芸亦认同此观点,亚洲人佩戴口罩的行为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一种公共卫生行为意识,体现了一种对疾病的认知观,以及对疾病传染途径的理解。1918年大流感在全世界暴发,为了控制疫情,日本朝鲜等地推行强制戴口罩措施。时至今日,戴口罩衍变成东亚社会卫生行为意识。戴口罩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行为,社会习惯。口罩对于预防流感疾病、预防传染病、预防空气污染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回溯历史,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曾开展大规模防疫宣传教育运动,提倡不吐痰,勤洗手、灭蝇灭蚊,推广疫苗接种。但是二战以后,主要提倡疫苗接种,别的防疫措施教育减弱,很少从社会公共意识层面推行卫生观念,只重视医疗技术,形成对医疗技术的绝对依赖,放弃了人在防疫中的作用。
公共卫生又如何演变为国家权力的概念?公共卫生的先进与否成为衡量国家实力强大或是弱小,文明先进或是落后的尺度。20世纪初,西方国家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性,用科学作为话语来衡量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统计科学成为一种重要的解读方式,人口死亡率成为国家先进与否的重要指标。这种文明进化论的思考模式让欧洲文明高度发达而非西方国家落后野蛮的大众认知进一步深化。深入剖析,欧洲人试图用种族主义来构建先进和落后的社会。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吸收了西方的种族主义,主张“强国强种”以保护羸弱的中国。“东亚病夫论”在彼时喧嚣直上,而此种论调,见诸于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者、外交官的日记、书信、报纸诸端,中国社会的脏乱差,环境污染严重,民不聊生的景象被记录下来,也成为传递到西方社会的唯一印象。时至今日,“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仍然被记录在美国人的书本和历史当中。随着海外交流的频繁,愈来愈多的域外学生来到中国访学交流,中国“东亚病夫”的污名化形象也由此正在逐步被打破。中国城市的绿化进程和生态保护措施,目前的生态环境“颠覆”了西方人以往的固化印象。文化交流的诸多努力,使很多外国人看到真实的中国。但是,有些人难改固有偏见,新冠疫情爆发后,在欧美国家再次出现“污名化”中国。
纵观20世纪,为了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推动政治革新、倡导社会改良运动,提出建立现代强国。推动公共卫生现代化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公共卫生现代化不仅要建立卫生机构、培训专业人员、更新技术,也要改变人们卫生意识、行为、态度等,这可以说是卫生现代化的硬件设施与社会软环境的两面观。中国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的形成就是卫生软环境的转变,其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晚清北洋时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卫生行为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公共卫生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时代特征。晚清北洋时期,改良和革命志士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用社会进化、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理论分析国家民族的盛衰、存亡,阐述个人国家命运一体,即国体论。为了探索强国之路,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认识到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国体论变成一种大众化的社会思潮。晚清人士李伯元曾在《文明小史》中以讽刺诙谐的笔法记录了时人对国体形象的认知。二十世纪初爱国学生走向街头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其中一段街头宣传如下:
“中国就像我,一个身体,十八个省就像我的四肢、头、肩膀。日本占领了我的头,德国占领了我的左肩,法国占领了我的右肩,俄国占领了我的后背,英国占领了我的肚子,还有意大利骑在我左腿上,美国骑在我右腿上。哎呀,我的整个身体都被他们瓜分了,你看我怎么活?”
严复、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改良和革命志士都在探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传统中国社会重文轻武的观念在巨大的变革时期遭到了强烈的冲击。“头脑发达,四肢简单”一度被视为圭臬。严复在1895年文章《原强》中提出发展民智、民力、民德是中国强大的基础。1905年的《东方杂志》曾提出“医学论”,告诫国人“卫生之重要,小之一人一家受疾病呻吟之苦,大之全国全种滔天演消灭之惨”。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刊文“我之爱国主义”,警告“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的“论体育”中不仅继续提倡德智体,还进一步阐述体育能够调和情绪,锻炼人的意志。许多青年学生参与到国家卫生建设的畅想当中。
公共卫生教育及宣传普及最初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地方精英联合举办。1914年开始,基督教青年会大力举办公共卫生讲座,讲座初设于上海,此后,基督教青年会逐渐发展出一系列以大城市为主的全国巡回演讲、卫生展览和宣传大会。基督教青年会及地方精英以“强国”为口号,倡导“卫生能生利”,而“生利”这一概念是直接移植于美国卫生观。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卫生宣传的本土化,讲堂悬挂大量标语,其中包括中国一贯强调的治国三大要素:人民、土地、政事,把治国与卫生宣传裹挟在一起,以唤醒民众认识卫生,培养民众卫生观,理解卫生与国家的重要关系。讲座现场的标语中还有“美国每年每千人死十四人”“英国每年每一千人死十五人”“德国每年每一千人中要死去十八”“英属印度国美千人要死三十三个”等,诸如此类的标语,用人口死亡率高低的统计数据说明国家的强弱、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对于中国公共卫生宣传,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死亡率要高于印度,这引发时人的不满。此外,一些报刊杂志刊载发行防疫措施,如隔断交通、隔离举措种种,通过媒体传播防疫观念。1918年,绥远鼠疫爆发期间,警察甚至一度在报刊上刊发广告鼓励民众捕捉老鼠,以钱财作为奖励,激励民众参与捕鼠运动。

四、卫生大众化:爱国卫生运动从城市到乡村的传播
自19世纪后期,西方的种族主义者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鼓吹白人至上主义,激化民族矛盾及社会矛盾。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经历了复杂的在地化过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是现代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提高民众的卫生知识和提倡个人卫生行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府提倡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同时结合三民主义国家建制框架,以宣传、训练、唤醒为三个阶段来提高大众卫生认知,构建现代的公共卫生机制。中国的社会精英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这些理论激发民众,提高竞争能力,实现强国强种的口号。譬如,举办讲座期间,广播主讲人会问,我们每天喊口号为民族国家复兴努力奋斗,但我们用什么力量去战胜敌人,实现国家复兴呢?答案是,第一要有高度优秀的民族素质,第二要有健康的身体。大众卫生认识也分为三个阶段,即宣传、训练和唤醒。在宣传阶段,民众接受卫生知识的方式包括口耳相传,以及培训教育。其次,在训练阶段,国民政府主要是种痘培训、强调体育锻炼、培训接生员,禁止不良卫生习惯;第三阶段,主要通过开展大型公共卫生活动,卫生游行等,官员参与街道的清洁打扫活动。与此同时,医疗卫生精英也将西方的人体机械论引入中国。学校卫生体系开始构建,学校医务室得以创办。学校鼓励学生参与打扫卫生,保持清洁活动,从小养成卫生习惯, 这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期。
共和国时期,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标志的卫生运动达到了高峰,宣传教育扩大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建设核心思想之一。建国初期,人口85%的文盲率是阻碍卫生知识教育普及的“拦路虎”。爱国卫生运动囊括了扫盲运动、科学发展、科普医学知识等等,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和社会变革意义。爱国卫生运动始于抗美援朝时期,美国人利用细菌战的消息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引发全民激愤。“细菌”成为政治隐喻,为了打倒“帝国主义细菌”,中国政府大力宣传推广爱国卫生运动。这场运动在全国展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广泛的政治宣传和社会宣传动员群众,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无论是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得到了全面而广泛的宣传。其次,是对疾病知识的宣传,提倡预防疾病, 保护健康。卫生海报无处不在,起到极大宣传作用,如防治疟疾的海报详细介绍了疟疾发病缘由、预防救助措施。大众科普卫生知识逐步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改变人们卫生习惯,演变成为一种公共卫生意识。第三以教育为媒介,传播卫生与疾病知识,以期达到改变民众的卫生认识和卫生习惯,促进民众卫生行为意识的转变。相较于民国时期,尽管卫生知识相差无几,但是宣传方式和内容大相径庭。民国时期,卫生宣传仅仅局限于大城市,宣传者是精英知识分子,宣传对象也仅限于有产阶级。共和国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波及范围更广,受惠民众更为广泛,宣传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尤为重要的是,卫生运动深入到乡村社会。为了推广爱国卫生运动,政府机关通过宣传海报、公共集会和家庭检查、鼓励捉蝇灭害等方式,将卫生知识渗透到民众的个人日常生活当中,使得卫生清洁成为民众日常生活所熟悉和了解的一部分。

总而述之,公共卫生概念和行为随着国家的变化不断发生演绎和阐释。晚清至北洋时期,卫生运动的兴盛与国家存亡休戚相关;民国时期,国家复兴是卫生运动的主题,高举强国强种的旗帜;共和国时期,爱国卫生运动是全方位的政治、卫生、人民健康和社会改造的全国性运动。
公共卫生的现代化进程和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加强不仅促进个人发展,也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人类健康。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显著提升,增长速度远高于欧洲、美国等其他国家,联合国近期报告,202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7岁。从长远看,新的病毒还会不断挑战人类,医学科学家需要严谨的研究才能弄懂病毒原理,对症下药,研制有效疫苗。在疫苗没有研制出之前,民众只能通过日常防疫手段保护自己及家人,减少病毒在社会上传染。如果民众有公共卫生意识,且公共卫生行为已成为日常习惯,整个社会就会积极行动起来抗疫防病,否则,正如2020年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所示,病毒在社会传播,民众防疫意识淡薄,造成严重生命损失。
五、学者与谈:公共卫生的另一种叙事
方小平教授认为卜丽萍教授对公共卫生概念的重新演绎,公共卫生的叙事再梳理,为我们打开了解释公共卫生措施的新面向。她主要聚焦于社会公德在公共卫生领域产生的影响力。除此以外,卜教授就晚清传教士、民国政府及共和国政府塑造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过程进行了梳理,这对当下医学史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卜教授的两地生活经验既为她理解中美社会的差异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她以比较视野看到中美卫生措施的异同,开拓了学术视野。若要理解中美当今防疫政策的巨大差异,回溯历史是一条必由之路。尽管近代公共卫生起源于西方,借由传教士传入中国,却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当中,推动卫生“隐喻”的驱动力也发生了变动。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生态环境急遽变化,为了应对一系列的环境和卫生问题,公共卫生概念应运而生。在中国的历史情境当中,公共卫生发展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一以贯之的主题。从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时期,涉及公共卫生意识觉醒与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之间的关联,如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从而体现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每一个阶段,精英知识分子的诉求和行为也是变化的,革命志士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民国时期,乡村卫生示范区的产生,比如南京的江宁和河北的定县这样具有的代表意义的示范区,对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新中国时期,国家大力消灭血吸虫,开展疫苗免费接种。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民众对公共卫生认知概念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公共卫生从一个模糊的概念逐渐具象化。总言之,公共卫生意识形态的塑造历经了宏观的合法性叙述到微观的制度建设;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公共卫生观念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不再被束之高阁;从区域来看,卫生意识行为历经了从城市到乡村,自上而下的落实;从普及的阶层来看,公共意识行为从精英知识分推介到普罗大众。
在方小平教授看来,中国的卫生意识行为的形成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国家治理能力、医学技术的进步、医学权威的建立、卫生制度的完善多方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为关键的因素是国家治理的全面实施和医学技术的进步。就国家治理而言,晚清民初时期,公共卫生意识行为意识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的探讨,如小规模的卫生展览、卫生防疫仅停留在观念层面的普及。民国时期,孱弱的国家力量也无法建立有效的防疫和治理体系,尽管有实验乡村计划和新生活运动诸如此类计划,但是这些政策在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防疫政策的构建并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防疫体系迅速在城市和乡村推广和实施,清洁卫生防疫的贯彻,如1960年代,为了东南沿海霍乱疫苗的全面接种,政府将单位工资的发放和疫苗接种挂钩,从而有效推动疫苗政策的实施。医学技术也是影响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医学史专家如方教授对霍乱的研究、刘少华对台湾麻风病的研究,美国学者郭瑞祺对肺结核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控制和消灭重大传染病时,倾向于采用传统的治疗方式,如检疫和隔离。国际学界认为诸如麻风、霍乱和肺结核此类传染病的诊治应该采取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的方式,资源的配置已然能够解决现实的疾病问题,无需再采用传统的隔离和检疫的方式。从此也可以看出,社会组织也是推动社会公共卫生行为意识塑造的重要推手。
在提问互动环节。高晞教授提问到,晚清以后,传教士与中国的早期科学家在考量一个国家卫生先进与否,都会用死亡率和生命率,这给中国社会带来种族危机感。这种被“制造”出来的种族灭绝的危机感敦促时人重视卫生建设,间接地改善了中国医疗体制,并最终推动中国人口寿命的高速增长。卜教授认可方教授提出来的国家治疗、医疗技术进步、社会资源配置在推动医疗条件改善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作为运作机制中的核心因素“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人既是国家治理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先进医疗技术执行者。审视美国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反应,可以发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决定此次新冠疫情能否得到有效遏制的关键动因。正如之前的演讲中提到的一样,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中国人均寿命极速增长,而这是欧美社会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完成的历史任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提高中国人均寿命这一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2020新冠疫情时期中美民众在防疫、自我保护等公共卫生行为方面表现迥异,反映了美国民众公共卫生意识薄弱,卫生防疫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能很好发挥,戴口罩是其中很明显的问题。
有学者就中国卫生贯彻实施的路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提出疑问——中国近现代公共卫生法律法规是否得到有效贯彻实施?政府具有何种程度的强制执行力?卜丽萍教授认为,中国公共卫生意识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初,受限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提倡和鼓励实施新型的卫生政策,以摘掉“东亚病夫”之帽,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卫生行政必然是自上而下在推行。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大型公共卫生运动,通过游行和宣传的方式,群众得以亲身参与卫生运动当中,这时便形成了“上”和“下”两种力量的合流。尤其在某些时期,政府会以“地方”作为试点,最终将地方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因而,检视近代以来中国公共卫生意识行为的形成,既要重视“上”也要强调“下”,既要看到其中一方的作用,又要看到两方的互动,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或者“二分法”。在法律层面,民国初期,政府已经开始建设相关卫生法律制度,制定严格的法规制度,相关的法律体系也是逐步健全完善的。
此次讲座,卜丽萍教授和方小平教授分享了各自的研究进展,为学界呈现了他们新近的研究动态,启发了受众对中国公共卫生意识形态生成问题的新思考。此番思考,既得益于诸多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也源于新研究路径的出现。此次讲座的召开不仅有助于推动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对国内外学者的对话以及医学史研究的反思都裨益良多。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