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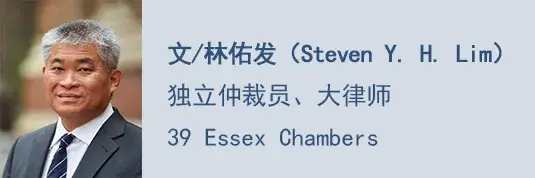
本文共计8,870字,建议阅读时间18分钟
1. 新加坡和英国的上诉法院近期作出的三份裁决,为重新探讨在普通法下,如何确定仲裁协议的合适准据法,提供了契机。在起草仲裁条款时,当事人往往会忽视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但在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时,对准据法的确认又至关重要。
2. 上述三项裁决分别是:
a) 新加坡上诉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公布的BNA v BNB and another [2019] SGCA 84一案判决(“BNA案”);
b) 英国上诉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公布的Kabab-JI S.A.L v Kout Food Group [2020] EWCA Civ 6一案判决(“Kabab案”);以及
c) 英国上诉法院于2020年4月29日公布的Enka Insaat Ve Sanayi A.S. v OOO “Insurance Company Chubb” and others [2020] EWCA Civ 574一案判决(“Enka案”)。
3. 目前已有很多文章讨论了BNA案和Kabab案,Enka案的裁决于近期2020年4月29日才公布。在本文讨论仲裁协议准据法的内容中,笔者将侧重于分析上述三个案例所展示的普通法下确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方法以及英国上诉法院在Sulamérica Cia Nacional de Seguros SA and others v Enesa Engelharia SA and others [2013] 1 WLR 102一案(“Sulamérica案”)中作出的裁决是否符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纽约公约》(“《纽约公约》”)以及《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示范法》”)项下的相应规定。
4. 另外,笔者还将讨论包括像英国、新加坡等这些“对国际仲裁最友好”的司法区法院在内的各国法院,在解释国际仲裁协议时是否充分注意了各冲突规范之间的多层次交互影响这一问题。
5. 限于本文的形式和篇幅,笔者仅指出了普通法判例规则与《纽约公约》的不同,并且就笔者看来,在解释国际仲裁协议时对冲突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该等问题因而留待未来通过更详细的论文予以阐述。
BNA案
6. 新加坡上诉法院于去年12月宣布了BNA案的裁决。该案涉及工业用气外销协议的三方仲裁,仲裁的三方当事人分别为:BNA(中国公司)、BNB(韩国公司)以及BNC(中国公司)。
7. 在最初的基础合同中,BNB是卖方,BNA是买方。BNB的关联公司BNC通过合同变更(“novation”)受让了BNB作为卖方在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并约定如果BNC未能履行合同义务,BNB需对该等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的准据法是中国法,也是该案争议的主要内容。
8. 仲裁协议中约定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根据中国法:(1)如果双方都是中国主体(例如BNA和BNC),则不能约定就争议内容在中国境外进行仲裁;(2)外国仲裁机构,即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能否在中国境内管理仲裁,在中国法下存在巨大争议。
9. 在该案中,仲裁庭的多数成员认为,根据“使之有效原则”(validation principle),新加坡法应是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使之有效原则”规定,如果仲裁协议在任一可能适用的法律下有效,则该仲裁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即使该仲裁协议在其他可能适用的法律下无效。[1]《纽约公约》中“有利于执行”的原则和冲突规则中也包含了“使之有效原则”。《示范法》中也存在类似规定。[2]
10. 仲裁裁决的多数意见理由如下:
a) 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逻辑角度,当事人都不会故意约定适用使仲裁协议无效的准据法。
b) “在上海仲裁”一词约定上海为仲裁庭审地(“venue”),而非仲裁地(“seat”)。
c) 当事人选择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为仲裁机构,因此新加坡是默示的仲裁地。
d) 新加坡法作为仲裁地法,应该是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综上,仲裁庭的多数意见认为仲裁协议有效。
11.第三名仲裁员的反对意见认为:
a) 上海是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
b) 因为中国法既是主合同的准据法,也是仲裁地法,因此不存在其他司法区法律可以替代中国法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适用。
c) 根据中国法,该案争议属于没有涉外因素的“国内”争议。
d) 中国法禁止外国仲裁机构对“国内”争议进行仲裁。
12. BNA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新加坡高等法院采用了其在BCY v BCZ [2017]3 SLR 357一案中确认的,英国高等法院Sulamérica案中确定的“三阶段分析法”。新加坡高等法院认定:
a) 当事人已明确约定适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5版,2013年)。该仲裁规则第18.1条规定,如果双方未约定仲裁地,则新加坡为默示的仲裁地。[3]
b) 仲裁协议涉及新加坡(依据仲裁规则第18.1条)和上海两个地点。在双方未明确指定仲裁地的情况下,“在上海仲裁”一词应被视为约定上海为仲裁庭审地[4]而非仲裁地。因此,结合仲裁规则第18.1条,新加坡应是默示的仲裁地。
c) 由于在中国法下本案仲裁协议的效力存疑,且新加坡是仲裁地,因此新加坡法应取代中国法,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适用。
13. 新加坡高等法院虽然维持了适用“使之有效原则”的多数意见裁决,但明确否认了新加坡法下存在“使之有效原则”。法院认为“使之有效原则”:(a)在本案中不能适用[5];(b)可能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相冲突[6];(c)新加坡法下已经存在“合同词句应当按照有效的而非无效的来解释”(verba ita sunt intelligenda ut res magis valeat quam pereat)的原则,即在解释合同时,应尽量按照条款有效而非无效来进行解释。[7](d)可能会造成在《纽约公约》下的执行障碍。《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A(a)项规定了仲裁协议准据法的冲突规则,其中首先考虑了当事人的约定;而“使之有效原则”旨在使仲裁协议有效,无须“对双方的法律选择给予必要考虑”。[8]
14. 笔者认为,法院似乎采取了一种技术主义的做法,将“在上海仲裁”认定为仲裁庭审地的约定而不是仲裁地的约定,从而裁决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新加坡法,使在中国法下本应无效的仲裁协议有效。法院虽未明确认定“使之有效原则”,但实际上却适用了“使之有效”的合同条款解释方法。
15. 实际上,“使之有效原则”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冲突,前者只会使得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发生效力。“使之有效原则”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A(a)项和第二条之间也不存在冲突,因为“使之有效原则”正是源自《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A(a)项和第二条的冲突规则以及“有利于执行”原则。[9]
16. 上诉法院在受理上诉时推翻了高等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认为:(a)对“在上海仲裁”的字面理解应是当事人双方约定仲裁地为上海;(b)因此,新加坡法院无权审理本案的管辖权问题。
17. 因与本案争议结果无关,上诉法院拒绝在判决中认定新加坡法下是否存在“使之有效原则”或“有效解释原则”的问题。[10](“有效解释原则”是大陆法系下与“使之有效原则”对应的概念,指在仲裁条款可以两种不同方式解释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使该条款有效的解释,而不是使该条款无效。)
18. 在作出这一裁断之前,上诉法院还适用了Sulamérica案中的“三阶段分析法”,即在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时,法院必须依次考虑以下因素:
a) 当事人是否有明确具体的法律选择?
b) 如果没有,仲裁协议是否存在默示约定的准据法?例如在Sulamérica案中,法院认为主合同约定的准据法可以推定为仲裁协议默示的准据法,但该推定可以被相反的证据所推翻。例如在仲裁协议根据主合同准据法下无效的情况下,仲裁协议默示的准据法应是仲裁地法。
c) 如果无法确定默示的准据法,则应考虑与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19. Sulamérica案中的“三阶段分析法”是根据一般英国合同法判例规则来判断准据法的方法,法院没有考虑这一标准是否符合《纽约公约》中的冲突规则。[11]Sulamérica案与《纽约公约》的规定有些许区别。《纽约公约》规定了默示约定的准据法为仲裁地法,但并未规定在无法确认明示或默示约定法律的情况下,应选择与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20. 如上所述,《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A(a)项中载有确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冲突规则,该规则与Sulamérica案的“三阶段分析法”相似,但是依然存在不同。第五条第1款A(a)项顺序适用:(a)“双方选择受其约束的法律”(包括明示和默示约定),(b)“如无任何约定”,则“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即仲裁地法)。《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A(a)项涉及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第二条涉及对仲裁协议的承认和执行。第二条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冲突规则,但从《纽约公约》的体系可以推断,为避免承认和执行仲裁协议和为避免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阶段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第五条第1款A(a)项的冲突规则应一并适用于第二条。[12]
21. 诉法院在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时并未充分考虑在解释国际仲裁协议时多种冲突规范之间的相互影响。法院没有明确说明在确定准据法时应适用何种法律下的合同解释规则,而是直接适用了新加坡法来解释仲裁条款并确定其准据法。法院据此认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中国法。但与其他合同一样,仲裁协议也应根据其准据法进行解释,也需符合《纽约公约》项下“有利于仲裁”原则和国际公认的合同解释规则[13]。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解释仲裁协议以确定其准据法时,是否应适用新加坡法[14]?
22. 笔者在新加坡的一次临时仲裁中担任仲裁员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该案就仲裁地是在新加坡还是在印度存在争议,而笔者被新加坡法下默认的仲裁员指定机构指定为该案的仲裁员,因此该指定仲裁员的程序是否正确也存在争议。案件的焦点在于“仲裁程序应在新加坡进行”(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held at Singapore)这一词句应理解为约定新加坡为仲裁地还是仲裁庭审地。
23. 申请人辩称,该约定仅是对仲裁庭审地的约定,仲裁地应是印度,因为印度法是主合同的准据法,而且(a)此类明示的法律选择应同时适用于仲裁协议;(b)即便不是如此,印度法也应是默示的准据法。根据Sulamérica案,在没有明确法律选择的情况下,主合同的准据法是仲裁协议的默示准据法;(c)同时,根据Sulamérica案,印度法与仲裁协议的联系最为密切。综上,由于仲裁协议和主合同都适用印度法,因此仲裁地应在印度。
24. 被申请人辩称,新加坡法是仲裁协议明示约定的准据法,也是默示约定的、或与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25. 因此,该案在仲裁协议的准据法认定问题上存在争议。笔者必须认定“仲裁程序应在新加坡进行”这一表达是否是对仲裁地或仲裁庭审地的明确约定。经笔者问询后,当事人同意适用新加坡法或印度法下有关合同解释原则。笔者判断当时没有必要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印度法还是新加坡法。如果此后就该问题产生了实质争议,笔者保留了在后续阶段重新裁定该问题的权利。在适用印度法和新加坡法(即英国法)下常见的合同解释原则后,笔者认定“仲裁程序应在新加坡进行”这一表达是约定新加坡作为仲裁地,而不仅仅是仲裁庭审地,因为:“仲裁程序”一词涵盖了从仲裁开始到最终裁决作出的整个仲裁过程,而不仅仅是庭审本身。“仲裁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当事人只是约定仲裁庭审地点,而不约定仲裁地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的情况。
26. 印度最高法院维持了笔者的裁决,驳回了仲裁地在印度,因此应根据《印度仲裁和调解法》(1996年)第11款指定仲裁员的主张。[15]
27. 回到上述问题,在解释某一仲裁条款以确定其准据法时应适用何种法律?笔者认为,为了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印度法还是新加坡法,应该在解释合同文本时适用国际通行的合同解释原则(并尽可能遵循《纽约公约》“有利于仲裁”的原则),并考虑当事人是否就仲裁地作出了明确的约定。
Kabab案
28. Kabab案涉及Kabab与首字母缩写为AHFC的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开发协议》(“FDA”)。FDA中的仲裁协议规定合同争议应由国际商会仲裁院(ICC)在巴黎进行仲裁。FDA中约定的合同准据法是英国法。AHFC随后成为了Kout的子公司。
29. Kabab根据FDA项下的仲裁协议对Kout提起仲裁。仲裁庭因而不得不考虑Kout是否属于FDA(包括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仲裁庭是否对Kout享有管辖权。仲裁庭的多数意见认定:
a) 法国法是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b) Kout是否受仲裁协议的约束应适用法国法。
c) FDA项下的实体权利义务是否发生转移应适用英国法。
d) 英国法下可通过当事人的行为推断Kout是否根据合同变更(“novation”)成为了主要的特许经营人。
30. 该裁决作出后,Kout在法国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Kabab在英国申请执行该裁决。英国高等法院判定:
a) FDA第14条明示约定了英国法是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b) 因此,Kout是否成为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应该根据英国法来判断。
c) 根据英国法,Kout不是FDA的一方当事人。
31. 经上诉后,上诉法院维持了高等法院的裁决:
a) FDA中的第1条,结合其项下第15条,应被认定为明确约定了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英国法。
b)第1条明确了“本协议”包括协议的所有后续条款,因此也包括第14条的仲裁条款。
c) 第15条明确约定,“本协议应适用英国法并依其进行解释”。因此协议项下所有条款,包括第14条的仲裁协议,均适用英国法。
32. 法院认为,主合同中的准据法条款一般不适用于仲裁协议[16],但本案中合同的第1条和第15条应结合在一起进行理解。
33. 笔者在Kabab案中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法院提出了一个问题:在Sulamérica案中的“三阶段分析法”或《纽约公约》中的冲突规则下,适用默示准据法是否应该以该默示约定必须满足商业效益为前提?但法院没有就该问题作出裁决。根据《纽约公约》的冲突规则,默示的准据法为(a)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或(b)仲裁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17]
34. Kabab的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Sulamérica案中的“三阶段分析法”并没有要求默示的准据法约定必须具有商业意义。法院依然对此存在疑问,并引述了最高法院在Marks& Spencer plc v BNP Paribas Security [2015] UKSC 72, [2016] AC 742一案中的判决:“如果Neuberger PSC法官在判决第14至32段确认了默示条款的法律,那么在满足该等条件的情况下,只有条款存在必要的商业效益的时候,该条款才能被视为默示条款。”[18]
35. 这一问题原因在于法院适用了英国普通法下的规则认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如Sulamérica案),即适用了一般英国合同法判例下确定合同准据法的规则。如上所述,这忽视了《纽约公约》中明确的冲突规则,但实际上包括英国在内的《纽约公约》的成员国都应该遵守该冲突规则。法院仅从英国合同法判例规则的角度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忽视了《纽约公约》所规定的冲突规则,包括其在没有明示约定法律选择的情况下规定的默示约定。综上,笔者认为,在认定仲裁协议准据法时,不应适用英国法中有关默示条款的法律,而应遵循《纽约公约》所确定的冲突规则。
Enka案
36. 本文的构思和写作是自 BNA案和Kabab案相继发布时开始的,但如果不加入Enka案的讨论的话,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是不充分的。
37. Enka案涉及违反仲裁协议的禁诉令(如Sulamérica案)。该案中,英国上诉法院需判断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英国法还是俄罗斯法,并据此判断是否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以及在俄罗斯启动的法院程序是否违反了仲裁协议。
38. 法院认为,在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的问题上,英国判例并未在仲裁地法和主合同准据法的适用顺序上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该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适用顺序进行澄清”的时候[19],“目前不确定的法律规范无法体现英国商事法中维持法律确定性以提高交易稳定性的原则。”[20]
39. 法院研究了涉及这一问题的主要判例,其中包括 Sulamérica案及Kabab案。在Kabab案中,法院表示,“只有在少数案件中,考虑到合同订立时的情况及合同文本适用的词句,主合同的适用法条款能够理解为对仲裁协议的准据法的明确约定”。[21]法院认为,Kabab案并不意味着法院普遍认定主合同明示的适用法条款的效力可以扩大到仲裁协议。
40. 法院认同了Sulamérica案中的“三阶段分析法”,但在确定仲裁协议默示的准据法,选择主合同准据法或仲裁地法时,法院作出了与Sulamérica案不同的认定,并就应该如何认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总结如下[22]:
a) 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应通过适用英国普通法冲突规范所要求的“三阶段分析法”来确定,即:(i)是否存在明示的法律选择?(ii)如果没有,是否有任何默示的法律选择?(iii)如果没有,仲裁协议与何种法律有最密切、最实际的联系?
b) 如果主合同中有明示的适用法条款,则可视为对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明确约定。主合同的适用法选择是否属于对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约定,取决于合同整体,包括其项下仲裁协议的体系结构,应该适用一般合同法(如果不适用英国法)的体系解释原则进行判断。
c) 在其他情况下,应推定当事人默示约定了仲裁地法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此为一般性原则。但如果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或案件的具体情况中存在强有力的反对适用条件时,可以适用其他法律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41. 据此,法院优先选择适用了仲裁地法,而非主合同准据法。理由如下:
a) 主合同的准据法应适用于主合同条款的效力、解释和履行,但不适用于独立的仲裁协议条款,这是由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原则”(doctrine of separability)决定的,而仲裁协议是否应适用“独立性原则”取决于仲裁适用法(通常是仲裁地法)的具体规定。主合同的准据法“对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几乎不产生效力,因为其指向的是独立于仲裁协议的主合同”。根据“独立性原则”,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存在性和效力都是与主合同分割开的,因此,主合同和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也应是相互独立的。[23]
b) 仲裁适用法和仲裁协议准据法的重叠进一步证明了两者通常应该是相同的法律。[24]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与仲裁适用法之间的联系比与主合同准据法之间的联系更密切。商事主体通常不应被认为会在两个密切关联的问题上(即仲裁协议准据法和仲裁适用法)约定适用了两个不同的法律。[25]
42. 就上述第一个理由,法院本身也承认了根据相关判例[26]和评述[27],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仅限于其有效性、存在性或效力,而没有完全使仲裁协议成为一份独立的合同。如 Enka案中引述,法官 Moore-Brick在Sulamérica案判决第26段中论述道:“独立性的概念本身只是反映了推定的当事人意思:即使主合同无效,其商定的解决纠纷的程序依然应该保持有效。其目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解决条款的法律效力,而不是使仲裁协议完全独立于主合同。”
43. 此外,《示范法》和《英国仲裁法》(1996)限制了“独立性原则”在仲裁协议的存在性和有效性上的适用:
a) 《示范法》第16条规定:“仲裁庭作出合同无效的决定,不应在法律上导致仲裁条款无效。仲裁庭可对其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裁定。为此目的,构成合同的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视为独立于其他合同条款。仲裁庭作出关于合同无效的决定,不应在法律上导致仲裁条款无效。”(强调为笔者后来添加)
b) 《英国仲裁法》第7条规定:“除非各方另有约定,构成或旨在构成另一协议一部分的仲裁协议(无论是否采用书面形式)不得因该等其他协议无效、未成立或已无效而被视为无效、不存在或无效,为此目的,该等仲裁协议应被视为一份单独的协议。”(强调为笔者后来添加)
44. 就上述第二个理由,法院也承认,只要当事人约定,仲裁地法院在仲裁协议中适用仲裁地法以外的“外国法”作为准据法理论上不存在任何障碍。[28]另外,如果仲裁地采用了《示范法》作为仲裁法[29],则仲裁地法院应依照“当事人所约定的法律或如果未约定,依照仲裁地法”[30]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认定。只有在没有明示或默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才默认适用仲裁地法。因此,《示范法》的体系中没有推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为仲裁地法。[31]
45. 法院同时认为,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仲裁地,适用仲裁地法作为仲裁协议准据法可能造成概念上的争议,因为英国的冲突规则不承认“浮动准据法”的概念,仲裁协议必须受在订立协议时可确定的某一法律制度的管辖。[32]
46. 尽管法院表示是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澄清适用法律的顺序”,但目前尚不能确定Enka案的裁决是否达成了这一目标。如法院所述,英国法判例在确定仲裁协议默示的准据法时应优先选择适用主合同准据法还是仲裁地法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定;但两个案件(即Kout案和Enka案)中法院均认为,如果推定适用的准据法将导致仲裁协议无效,则可推翻该等推定。
47. 当仲裁协议在某一可能适用的法律下无效时,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确定将至关重要。与其规定默示的准据法,不如明确适用旨在使仲裁协议生效的“使之有效原则”,这样才更有意义,也更透明。这不仅实现了当事人的商业意图,即约定一种有效可行的国际争议解决机制,也是《纽约公约》第二条和第五条第1款A(a)项以及《示范法》第8条、第34条和第36条的条款和宗旨所要求的。
结论
48. 本文没有更多篇幅来具体探讨笔者提出的例如《纽约公约》项下的义务、普通法与该等义务的差异,及法院解释国际仲裁协议时未充分考虑冲突规范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待更长篇幅的阐述及更为深入的探究,本文旨在提出并强调上述问题以促进讨论。
注释:
[1] BNA v BNB [2019] SGHC 142,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书第51段,引述了Gary Born:《国际仲裁协议准据法:国际视角》(“The Law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2014) 26 SAcLJ 814 ,第51段。
[2] 参见下文第15和47段中对“使之有效原则”的讨论。
[3] 该条款在2016年第6版中被删除。当前版本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中没有规定默示仲裁地。
[4] 在国际仲裁中,仲裁庭出于方便考虑可以在仲裁地以外的地点举办庭审。在仲裁的语境下,该地点被称为“仲裁庭审地”。但是法律上仲裁的“仲裁地”不会因为庭审在其他地方举行而改变。
[5] BNA案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书第53段。
[6] 同上,第55段。
[7] 同上,第62段。
[8] 同上,第65段。
[9] Gary Born:《国际仲裁协议准据法:国际视角》(2014) 26 SAcLJ 814,第27、56和59段。参见下文第19和20段对《纽约公约》第二条和第五条第(1)款第(a)项冲突规则的讨论。
[10] BNA案判决书第95段。
[11] Sulamérica案判决书第9段:上述问题未在判决中详细论述,当事人似乎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
[12] Gary Born:《国际仲裁协议准据法:国际视角》(2014) 26 SAcLJ 814,第30和59段。
[13] Gary Born:《国际商事仲裁》第二版,第9.05章。
[14] Gary Born认为解释仲裁协议时不应该适用仲裁裁决执行地国家的法律。同理也不应该适用仲裁地法律。
[15] 见Pricol Limited v Johnson Controls Enterprise Ltd. & ors案,印度最高法院民事初审法院仲裁案件(民事)2014年第30号(未公开)。
[16] 法院引述了Arsanovia v Cruz City 1 Mauritius Holdings [2012] EWHC 3702 (Comm); [2013] 1 Lloyd’s Rep 235 一案判决第21段。
[17] Kabab案判决书第70段。
[18] 同上,第53段。同时参见第54段法院关于法律上是否存在默示条款的论述。(法院认为,该观点可以“立刻被驳回”。因为上述争议只属于合同解释的问题,默示条款作为条款不会被“依法”被纳入到合同中。)
[19] Enka案第69段。
[20] 同上,第89段。
[21] 同上,第90段。
[22] 同上,第105段。
[23] 同上,第92和94段。
[24] 同上,第96段。
[25] 同上,第99段。
[26] Sulamérica案判决书第26段;另见BCY v BCZ案判决书第60和61段。
[27] Glick和Venkatesan:《选择仲裁协议的准据法》(“Choosing the Law Governing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载于Kaplan和Moser著《国际仲裁的可裁性和冲突规则》(“Jurisdiction Admissibility and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2018),参见该文章第9.05段。
[28] Enka案判决述第99段。
[29]《示范法》下的仲裁协议准据法冲突规则与《纽约公约》项下规则一致。
[30]《示范法》第34条第(2)款第(a)(i)项。
[31] 另见BCY诉 BCZ案判决书第64段。
[32] Enka案判决书第103段。
*林佑发先生是一名独立仲裁员兼大律师,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等机构中常年担任仲裁员,曾多次作为首席律师代理仲裁案件,在处理印度和太平洋司法区案件上具有丰富经验,擅长涉及建设工程、基础设施和能源的商事仲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