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除了疫情,我们最关心的应该就是「 蝗 灾 」了。
2019年6月起,东非地区便已出现大规模蝗灾。最开始,当地人无力反击,灾情愈演愈烈。
紧接着,4000亿只蝗军顺着季风浩浩荡荡来到南亚,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今天还看到一则新闻: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
消息一出,网上一阵叫好。
照理说鸭子捕蝗能力强,身手灵敏,抱团作战,纪律严明,擅长地毯式攻击。大家很容易就脑补出「10万鸭军和蝗虫正面对垒」的情景。

遗憾的是,这些鸭子面对的,可是数量高出自己数十万倍的满天飞蝗。单凭鸡鸭大军就想成功?实在是有些杯水车薪。
对于年轻人来说,蝗灾离我们的生活似乎很远。或许也有人会乐观地认为:这一次,我们可以轻易战胜。
这种乐观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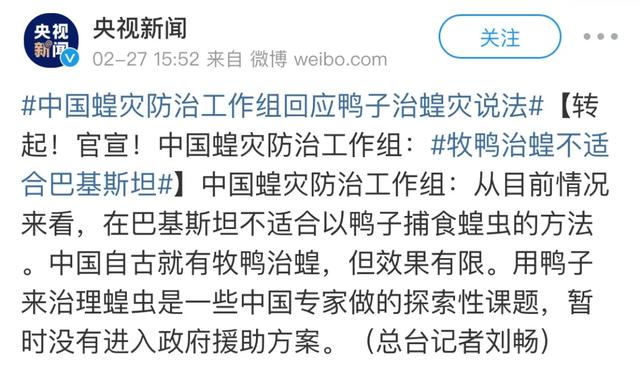
或许你会想:没关系的,蝗虫生命周期短,3个月之后就好了。
万万想不到的是,它们会在迁徙过程中拼命繁衍族群。一只雌性蝗虫,一次性就可以产100颗卵左右。
所以,哪怕是上一代死去,新生一代也会刚好长成。只要破土飞出,就会继续壮大族群,演化成覆水难收的灾难。

不仅如此,我们熟知的蚂蚱和这次成群作战的蝗军相比,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绿色蚂蚱往往是独居,性格温顺害羞,主打猥琐发育,难成气候。

不仅如此,它们还会释放一种叫苯乙腈的化合物,然后转化成氢氰酸。
氢氰酸具备刺激性,对于蝗虫的天敌鸡鸭鸟来说,吃下蝗虫可能会中毒。
轻则恶心呕吐,重则失去知觉,甚至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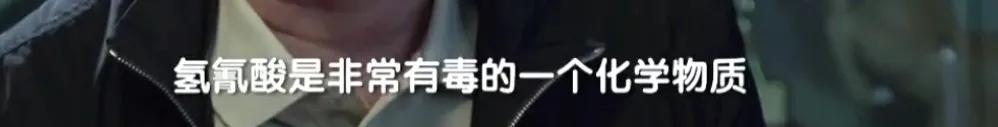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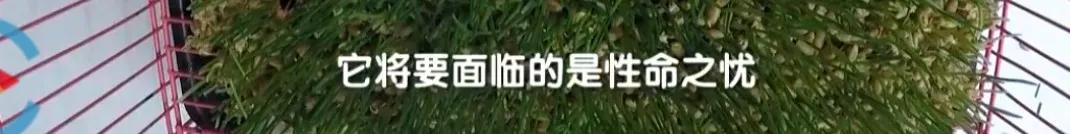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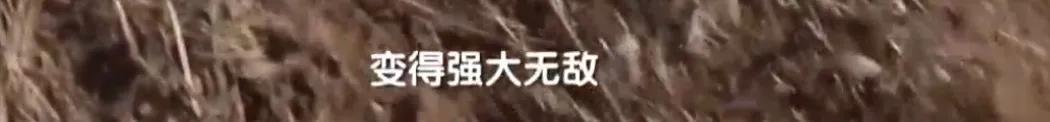


你看,为了让自己活下来,蝗虫真的是煞费苦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千年来,人类在面对蝗虫时依旧如此头疼的原因。
02
面对目前这种千亿数量级的蝗灾,我们只能用大范围喷洒药物的方式遏制其发展。
比如用飞机喷洒药物,可这样高效却不环保。虽然消灭了蝗虫,却会损害农作物和其他动物的健康。
最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闹得两败俱伤。


在鸡群种类中,珍珠鸡出类拔萃,啄法快很准,蝗虫简直是天然饲料,把自己养的白白胖胖后还会被送上餐桌,为当地家禽业贡献一份力量。
可鸡群内也会发生内斗,它们没有集体意识,有时候还不太听指挥。
于是我们的农业工作者将目标锁定在鸭子身上。
它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擅长地毯式作战,可以对蝗蝻(幼虫)从土地里连根拔起。

习惯了富足生活的人,根本不敢想象:农民累死累活忙了一年,结果蝗灾入境,庄稼被洗劫一空,一年到头颗粒无收。损失多少不说,很可能连命都没了。
所以你会看到那句熟悉的打油诗:
“蝗虫爷爷行行好,莫把谷子都吃了,众生苦劳了大半年,衣未暖身食未饱,光头赤足背太阳,汗下如珠爷应晓,青黄不接禾伤尽,大秋无收如何好,蝗虫爷,行行好,莫把谷子都吃了。蝗虫爷行行善,莫把庄稼太看贱,爷爷飞天降地时,应把众生辛苦念。
那个年代我们经历的,其实就是如今非洲贫困地区所面对的。
为了战胜蝗灾,你知道中国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一开始,我们没有先进的工具和治理理念,只能用铁锹拍打驱逐。

再后来,我们引进了飞机喷洒农药的技术。我们封山育林,完善水利设施。我们创立了网络熟知的「鸡鸭大军」的生物防治体系。
每一步,都看似理所应当。
每一步,也都何其艰难。
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因过劳生疾退休了。有的人奋战几十年,去世的时候在互联网上没有任何回响。
2020年2月14日,著名生态学家、对蝗虫治理作出巨大贡献的孙儒泳先生,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我们现在之所以不会对蝗灾心生恐惧,是因为农业工作者如今依旧在田野里治虫害,是科研人员毕其一生于一役,终日埋头实验,忍受着群居性蝗虫的刺激气味。
他们就是为了让我们父辈祖辈辛苦种下的粮食不被糟蹋,为了让人不至于因饥饿而死。他们前去异国支援,就是怕有一天蝗灾侵袭中亚地区,后果不堪想象。

老话说:“老一辈视蝗虫如瘟神,父母一辈视蝗虫如零食,我辈没见过几次蝗虫。”
不是我们见不到。
而是那些能见到的人,将蝗虫死死封锁在你我的生活之外。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我们能坐享其成,更要心存敬畏。
“请不要小看任何一场灾难,因为这背后的代价实在太大。
哪有什么天佑中华,是无名英雄在默默守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