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唐琼琼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学院,上海201620)
摘要:我国的商事调解存在基本法缺位、调解员认证机制缺失以及调解员职业守则统一化、国际化程度不足等制度性问题,其弊端将在《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生效后显现,迫使法院不加区分地承认商事类争议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而其中某些类型的争议可能是我国立法本无意授权调解予以解决的,这损害了国际商事调解的正当性,减损了调解对于当事人的吸引力。为此,我国应当制定一部商事调解基本法,就可调解事项、调解的保密性以及和解协议的执行等当前立法盲点问题作出规定;引导民间机构建立调解员认证机制;制订调解员职业守则范本,并将职业守则的遵守情况与调解员认证挂钩;以调解员认证和职业守则为手段整合机构调解、律师调解和行业调解,推动我国一体化市场调解机制的形成。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商事调解;认证;职业守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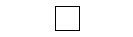
调解制度由来已久,运用调解解决纠纷的思想在东西方皆源远流长:儒家的“礼”治思想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古罗马也有“消灭诉讼对国家有益”的法谚。[1]当今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调解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然而,各国家和地区在调解立法及其配套制度方面的差异显著。除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UNCITRAL)于2002年制定的《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外,针对调解的国际立法长期以来处于法律盲区。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面作用的发挥。
2014年5月,美国向UNCITRAL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建议,提议由其第二工作组以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之可执行性为主题拟订一部多边公约,以鼓励当事人更多地使用调解。UNCITRAL于2015年第四十八届会议授权第二工作组启动该主题的工作。第二工作组历时近三年,形成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草案文本以及《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2018 年(修正 2002年《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的草案文本,提交UNCITRAL审议。2018年6月25日,UNCITRAL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两个草案文本,决定将调解公约草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 并建议各国在制定或修改调解的相关法律时参考调解示范法。鉴于新加坡在UNCITRAL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倡议为公约举行一个签约仪式并由新加坡承担签约仪式的相关费用,会议建议将该公约简称为《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18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约》。[2]《公约》按计划将于2019年8月7日起对所有国家开放签字。《公约》生效后,将对成员国提出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等要求。
跨国诉讼、仲裁和调解是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主要手段,两者已有《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分别作为各自跨国承认和执行的国际法依据,在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预见,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生效和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国际商事调解的运用将更为普及。加强对《公约》本身及其对我国影响的研究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旨在梳理我国的商事调解立法及其配套制度,探明我国加入《公约》存在哪些潜在的制度性障碍并寻求应对策略,为《公约》在我国的适用铺平道路,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一
《公约》的基本要求及我国民商事调解法律制度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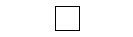
根据《公约》第1.1条的规定,《公约》适用于调解所产生的、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在订立时具有国际性的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和解协议”)。其适用范围受三个概念的影响:商事争议、书面形式、国际性。《公约》未对“商事争议”进行定义,但在第1.2条进行了穷尽式的除外列举:一是消费者因个人、家庭或家居目的而进行的交易所产生的争议之和解协议;二是与家庭法、继承法或就业法有关之和解协议。除此之外,通常含义上的“商事争议”都在《公约》的适用范围内。① 《公约》第 2.2条对“书面形式”的要求是“以任何形式记录”和解协议的内容,电子通信只要可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和解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公约》为和解协议“国际性”的判断设置了三项参考要素:营业地、实质性义务履行地、最密切联系地。如果在和解协议订立之时,至少有两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或者协议各方当事人设有营业地的国家与和解协议所规定的实质性义务履行地所在国不一致,或者协议各方当事人设有营业地的国家并非与和解协议主体事项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则该和解协议具备国际性。据此,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的涉外商事争议以及个别纯国内争议,如果经调解达成了和解协议,则成为《公约》意义上的“国际和解协议”,当事人有权按照《公约》的规定申请成员国承认该协议的效力。
我国加入《公约》并且《公约》对我国生效后,我国将承担两项基本义务:一是在当事人向我国法院申请执行一个国际和解协议时,我国法院应根据《公约》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予以执行(《公约》第3.1条);二是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一项已经通过调解达成了和解协议的争议时,我国法院应当准许另一方当事人根据《公约》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援引该和解协议,以证明相关争议已经得到解决(《公约》第3.2条)。《公约》对国际和解协议的承认和执行并未设置实质内容上的限制,仅在第4.1条提出了形式上的要求:申请人须提供由各方当事人签字的和解协议,以及该和解协议是经由调解程序所产生的相关证据(例如和解协议上有调解员的签名、调解员签字的文件上显示进行了调解、管理调解程序的机构出具的证明等)。只有在《公约》明确列举的有限情形下,②我国法院才能拒绝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申请,或者拒绝接受当事人援引国际和解协议对抗另一方的诉讼请求。与此同时,涉及我国当事人的国际和解协议,可以在《公约》的其他成员国得到执行,或者在国外诉讼程序中被援引作为抗辩。如果我国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无法与《公约》实现良好的衔接,将促使当事人放弃调解这一选项或者选择去其他调解友好型的国家进行国际商事调解,③ 也给当事人滥用调解程序规避司法管辖留下了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照《公约》的要求对我国的调解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梳理,以促进商事争议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解决。
我国民商事调解的现行法律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有关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包括 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人民调解法》、1989年国务院制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18年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二是以调解方式解决特殊类型争议的法律,例如2007年、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2018年国务院制定了《医疗争议预防和处理条例》,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三是涉及司法与调解相互关系的法律,例如《民事诉讼法》第八章、第十五章第六节对法院在诉讼程序中主持的调解、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各自作出了规定,最高院针对调解问题先后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2011年)、《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2016年)。
我国以《人民调解法》为核心的人民调解制度体现出了较强的行政主导色彩:人民调解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管部门、以基层人民法院为业务指导部门(见《人民调解法》第 五条);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受司法部、 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这一特点使得人民调解制度在国内民事争议的解决方面更容易发挥作用,而在商事争议解决方面的优势不突出,对涉外商事争议的外方当事人吸引力更为有限。我国以《民事诉讼法》第八章为核心的法院调解制度带有浓厚的裁判色彩,倾向于在“事清责明”的基础上进行裁判式调解,[3]减损了调解先天具有的民间性、自愿性优势,④也不易被涉外商事争议的外方当事人所接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调解法律制度“行政化色彩浓郁”,[4]侧重于纯国内争议特别是民事争议的化解,而非商事争议的解决。
注释:
①以国家、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也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 但《公约》第8.1条允许缔约国随时以声明的方式对此作出保留,选择在声明规定的限度内适用《公约》。
②公约第5条将缔约国的主管机关拒绝提供救济的理由分为两类情形:一是主管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拒绝提供救济,二是主管机关依职权主动拒绝提供救济。前者包含的事由有:
(a)和解协议的一方当 事人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状况。
(b)和解协议(i)根据当事人有效约定的和解协议的管辖法律,或者 在无相关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收到申请的缔约国主管机关所认为的应予适用的法律,无效或无法执行;或者(ii)根据其条款不具约束力或者不是最终的;或者(iii)随后被修改。
(c)和解协议中的义务已得 到履行,或者义务不清楚或无法理解。
(d)准予救济将与和解协议条款相冲突。
(e)调解人严重违反适 用于调解人或调解的准则,若非此种违反,该当事人本不会订立和解协议。
(f)调解人未向各方当事人 披露可能对调解人中立性或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形,并且此种未予披露对一方当事人有实质性影 响或不当影响,若非此种未予披露,该当事人本不会订立和解协议。
后者包含的事由有:
(a)准予救济 将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
(b)根据该国法律,争议事项不得以调解方式解决。
③成员国承担《公约》项下的义务并不以调解程序地为公约的另一成员国为前提,因此,如果我国加入了公约,涉外商事争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去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调解,之后依据《公约》申请我国法院承 认或执行该和解协议。有学者认为这将导致公约成员国义务的不平衡。参见:葛黄斌《〈新加坡公约〉的普惠红利是一把双刃剑》,见《法制日报》2019年2月19日。
④例如,法院调解的案件大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参见:李浩《当下法院调解中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调解案件大量进入强制执行研究》,见《法学》,2012年第2期,第139-148页。
二
《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面临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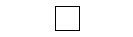
如果《公约》对我国生效,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将按照《公约》的规定得到认可。无论是国际商事调解程序在我国境内的进行,以及经此类程序所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还是境外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均将考验我国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与《公约》的匹配度。一方面,我国商事调解一般性立法的缺位使得与调解相关的具体法律制度存在空白或不足,将给《公约》在我国的适用造成障碍;另一方面,我国商事调解配套机制的严重不足,将打击国际商事争议当事人运用调解解决争议的积极性。
(一)与民商事调解相关的具体法律制度存在空白或不足
由于我国没有针对商事调解的一般性立法,与调解相关的某些具体法律制度存在空白或不足,将给《公约》在我国的适用带来多重阻碍。
首先,我国立法并未明确可调解事项或不可调解事项的范围。《公约》第1.2条将消费类争议以及家庭、继承、就业类争议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并在5.2(b)条将“本国法认为争议事项不可调解”列为法院主动拒绝提供救济的两项理由之一,凸显了“可调解事项范围”的重要性。然而,我国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的相关规定并未涉及可调解事项的范围问题,其他有关调解的专门性法律也仅就特定类型争议适用调解进行个别规定。可见,我国并无针对可调解事项的一般性规定。与我国不同的是,在制定了调解基本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会明确可调解事项的范围。例如,欧盟《2008/52/EC号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方面的指令》(以下简称欧盟《调解指令》)第1.2条规定,本指令不适用于根据相关准据法不得由争议当事人自行处置的权利和义务相关的事项,尤其是税收、海关、行政事项,或者因行使或怠于行使国家权力而引发的责任。[5]又如,香港《调解条例》附表1列举了12类不适用于该条例的程序, 包括劳动、婚姻、性别歧视、残疾歧视、种族歧 视等特别法有所规定的程序。[6]在我国立法未就可调解事项的范围作出系统性规定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将迫于《公约》的要求去承认那些立法本无意允许调解加以处理的特定类型争议所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
其次,我国立法未就调解的保密性作出规定。保密性是调解的先天优势之一,各国调解法一般都涉及保密问题,对有关主体在调解过程中所获知的信息之披露及该信息在后续程序中之使用进行限制。例如,欧盟《调解指令》第7条第1款规定调解的保密性受法律保护,同时授权成员国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允许调解员或参与调解程序管理的人员在民商事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中提供调解程序中所获取的信息作为证据。又如,非洲商法协调组织2017年制定的《统一调解法》第10条规定:调解程序中的所有信息均应保密,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法律要求进行相关信息披露或者因执行调解所达成协议之必须而进行相关信息披露。[7]虽然该条未明确保密义务的主体范围,但从第 11条对调解程序中的信息在后续仲裁或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之限制来看,① 保密义务的主体范围应包括案件的当事人、调解员以及含调解程序的管理人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人。再如,新加坡《调解法2017》第9至11条着重规定了保密问题:原则上,调解过程中的信息(包括调解 过程中的口头表述、为调解准备的文件以及任何其他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仅在调解各方同意的情况下,法庭或仲裁庭依该法第9(3)条所设定的条件批准的情况下,以及其他有限的例外情形下,方可向案件以外的第三人披露调解过程中的信息;调解过程中的信息不得在其他诉讼、仲裁或纪律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除非法庭或仲裁庭应申请,根据该法第11(2)条的规定批准此种使用。[8]遗憾的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未明确提及调解的保密性,② 虽然相关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更侧重调解程序的保密性, 而忽视了调解信息的保密性。[9]保密性本应是调解较之于司法解决的优势之一,立法应最大限度地保护调解的保密性,[10]如果调解保密性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就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不利于调解的推广运用和《公约》目的之实现。
最后,我国立法有关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之可执行性的规定与《公约》的要求不符。我国立法将经调解所产生的争议解决结 果区分为调解书和调解协议,前者被赋予了强制执行力,后者则需经司法确认方具有强制执行力。《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必须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据此,调解书只要满足立法所规定的生效条件,即具有强制执行力。与此不同的是,经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公约》称为 “和解协议”)在我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除非该协议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 和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得到了司法确认。尽管《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调解 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法院在实践中却往往沿用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 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内容,将人民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合同处理,可因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而否认该协议的效力。虽然人民调解协议之外的非诉调解协议是否属于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对象仍存在理论上的争议,但司法实践坚持将经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全部纳入司法确认程序的范围。[11]法院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时,不仅对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还对其进行内容上的审查,这与《公约》对成员国的要求相悖。《公约》的核心要求是,成员国应认可符合第 4.1条形式要求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公约》对成员国拒绝提供救济之理由的规定是在《纽约公约》第5条的基础上拟定的,[12]与《纽约公约》允许成员国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相似。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外国仲 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其承认与执行尚且存在较多的误区,[13]我国现行立法就和解协议执行之规定的不足更注定了《公约》在我国适用时的水土不服。
综上,我国民商事调解的现行立法不足以满足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需求,更无法应对我国加入《公约》后国际商事争议调解所面临的新形势。
注释:
①第 11条规定:调解程序的当事人、调解员或任何其他人(包括那些与调解程序管理有关的人),不得在仲裁、司法或类似程序中提供以下任何事项作为证据:
(1)邀请当事人进行调解或当事人愿意参与调解程序的事实;
(2)当事人在调解期间就可能解决争议所表达的意见或建议;
(3)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或承认的事实;
(4)调解员或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建议;
(5)一方当事人已表示准备接受调解员或另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和解建议之事实;
(6)仅为调解程序而形成的文件。上述信息,无论其载体或形式如何,均不得作为证据提出,否则仲裁庭或法庭有权拒绝接受;仲裁庭、法庭或政府机构不得下令披露上述信息;受保密义务约束的信息不包括调解程序之前已经存在的证据。
②虽然《人民调解法》第十五条禁止调解员泄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的范围要窄于调解保密性所要求保护的信息范围。
(二)调解员统一资质要求与认证制度缺位
我国《人民调解法》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定性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① 并不强调调解员的专业资质。2018年4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细化了人民调解员的选任条件,要求民政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把人民调解员纳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和职业水平评价体系。该文件所体现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思路顺应了我国国内民事争议调解的需求,却与国际商事争议的调解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例如,该意见只要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我国的法院调解程序一般由受案法官主持,法官的任职资格及执业经验与国际商事争议调解员的素质要求也存在较大差距。2018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对诉至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商事争议案件,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纳入该机制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在调解机构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国际商事法庭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或者应当事人的请求依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该通知旨在将国际商事诉讼与仲裁、调解等非诉解决方式有机融合,但受制于商事法庭本身的司法属性,其对外方当事人的吸引力势必有限。更值得关注的是,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七家机构并未遵循统一的调解员任职要求,调解员的水平和调解的质量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国际商事调解与国内民商事调解对调解员的素质要求截然不同。国际商事调解的调解员除应具备国内民商事案件调解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外,还需具备外语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最好还要对大陆法和普通法的体例、 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以跨文化沟通能力为例,文化背景将影响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与双方当事人的互动,例如与双方当事人建立友好互信的关系,理解双方当事人的需求和利益诉求,理解当事人的身体语言和其他交流的信号,理解当事人的谈判行为及谈判策略;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在谈判中的作风差别很大,美国人是高度结果导向型的谈判参与方,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人员则更重视谈判过程,并且谈判中的人际关系体验往往直接影响到谈判的结果。[14]如果我国的调解员不具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沿用国内调解中惯用的思路、方式来主持国际商事调解,将很难被外方当事人接受为调解员,更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调解结果。
在商事调解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调解员的资质及其认证是调解最重要的配套制度之一。例如,《奥地利调解法》规定了调解员注册制度,授权奥地利联邦司法部负责维护注册调解员的名单。[15]近年来,我国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争相在商事争议解决的配套法律制度方面进行革新,以促进其纠纷解决服务中心战略目标的实现,[16]两者均在调解员资质及认证制度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2010年,香港律政司牵头设立的调解专责小组发布了《调解工作组报告》,提出了从监管制度的建立、调解员的培训与认证、调解公众知晓度的提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香港商事调解制度的建议,[17]该建议得到了采纳并陆续实施。在调解员的培训与认证方面,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律师会、香港调解中心、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 2012年8月联合发起设立了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Hong Kong Mediation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Limited,以下简称为 HKMAAL),作为香港唯一的调解员认证机构。HKMAAL分列“一般调解员”和“家事调解员”两类名单,两者有各自独立的认证程序,其认证旨在实现三重目标:一是为香港的调解实践设置职业标准的最低门槛;二是帮助公众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既有的调解资源;三是促进已认证调解员专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18]新加坡议会于2017年1月10日通过了《调解法2017》,新加坡法律部于当年10月份制定了补充性的《调解规则2017》,并指定新加坡国际调解协会的认证机制为“经批准的认证机制”(approved certification scheme),从而有权进行调解员的资格认证。要取得新加坡国际调解协会的认证调解员(Certified Mediator)资格,必须完成该协会的培训项目,具备一定量的前期调解经验,通过协会的知识和技能评估,[19]以确保调解员具备调解所需的基本素质。
调解员统一资质要求与认证制度的缺位使得调解的质量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将给当事人在我国获取高水准的国际商事调解服务造成障碍,把有意通过调解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当事人推向境外的调解机构或调解员。
注释
①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推选产生, 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组织推选产生。
(三)调解职业守则的统一化、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
《公约》第5条第1款(e)项规定,如果调解人严重违反适用于调解人或调解的准则,若非此种违反,该当事人本不会订立和解协议,那么主管机关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拒绝提供救济(即可以拒绝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申请,或者拒绝在诉讼中接受一方当事人以国际和解协议作为抗辩的理由)。在《公约》起草过程中,“准则”(standards)一词的理解曾引起代表们的讨论。①第二工作组最终决定暂不明确这一概念的含义,留待 UNCITRAL进一步立法。[20]《公约》的立法过程凸显了“适用于 调解人或调解的准则”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该问题上,既有在UNCITRAL层面形成国际性法律文件之必要,也有在各国层面制定法律或专业协会行为守则之必要。
调解员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操守问题不仅在理论层面引起了关注,[21]也在调解实践中受到重视,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前文提及的香港调解专责小组于2010年制定了《香港调解守则》,该守则所规定的调解员义务涵盖五个方面:公正对待各方当事人,与调解事项没有利益冲突,不得对任何一方有偏见,保障双方当事人有合理的机会与调解员进行沟通,确保当事人获取与调解程序相关的信息。该守则被香港多家调解服务机构所采用。例如,作为香港唯一的调解员认证机构的HKMAAL要求其认证调解员遵守该守则,并建立了针对调解员不当行为的投诉机制,违反该守则的行为或不作为将通过该投诉机制得到审查,如果最终认定被投诉的调解员有不当行为,则HKMAAL有义务将其从所有的认证调解员名录中除名。无独有偶,作为新加坡唯一的调解员认证机构的新加坡国际调解协会(以下简称SIMI)也制定了《SIMI调解员职业守则》。②该守则规定:SIMI调解员必须承诺遵守某一个 调解行为守则,并在被当事人任命之前告知当事人该信息;如调解员未选择其他调解行为守则,则该调解程序将自动适用《SIMI调解员职业守则》。为增强该守则对调解员的约束力,SIMI还制定了《SIMI调解员职业行为评估》,调解案件的当事人可以据此对调解员进行投诉,被认定存在违反职业守则行为的调解员将面临书面警告、暂停1年SIMI调解员的资质、永久取消SIMI调解员的资质等不同程度的处罚。
我国部分调解机构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调解守则,但其统一化、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例如,作为首批被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七家机构之一的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其《调解员守则》第四条规定:“调解员应当引导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秉承‘在商言商、以和为贵’的精神,逐步减少分歧,达成和解协议。”[22]上海金融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守则》第四条规定:“调解员应当引导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秉承‘互谦互让、和气生财’的精神,达成和解协议。”[23]这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规则有其可取之处,但却可能令外方当事人费解。总体来看,我国各调解机构调解员守则的内容不一,且内容普遍比较单薄,国际化程度不高。
在我国商事调解基本法缺位以及调解员职业行为守则不到位的情况下,即便国际商事调解的调解员在调解程序中的行为有不当之处,我国法院也难以依据《公约》第5条第1款(e)项之规定拒绝提供救济,从而损害国际商事调解的正当性,进而影响国际商事争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解决争议的积极性。
注释:
①在第二工作组第 66届会议上,有代表要求澄清“准则”一词的范围和含义。对此有三种意见:一是准 备工作文件或随附公约的任何解释材料可提供适用准则的例子,不仅应当提及不同类别的准则,还应当提及这些准则所含的要素,如《调解示范法》第 6条第(3)款及其《颁布和使用指南》第55段提到的独立性、公正性、公平对待以及保密性;二是在文书案文中保留这些概念;三是建议UNCITRAL单独编写一份调解人行为守则。参见:第二工作组(争议解决)66届会议(2017年2月 6日至 10日,纽约)工作报告,A/CN.9/901,para87
②守则原则上要求调解员符合SIMI调解员认证的标准,并具备处理特定案件的能力。具体来说,守则的要求涵盖四个方面。第一,调解员自我营销的相关信息真实,不具有误导性。第二,调解员应在接受调解任命前告知当事人:调解员的背景和经验,SIMI调解员应遵守的行为守则,当事人认为调解员的行为不符合守则要求时的处理程序,各方当事人在调解程序结束时将被邀请就调解过程及调解员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书面反馈,经请求告知当事人自己是否有职业责任保险的保单;可能影响调解员独立性、中立性或公正性的信息,以及可能与调解相关的利益冲突之信息。第三,调解员应以独立、中立及公正的方式行事;如在调解过程中产生了影响调解员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或者与有关主体利益冲突的新情 势,则调解员应尽快告知各方当事人,并提议退出调解程序,非经调解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员不得继续该调解程序。第四,调解员应确保当事人对调解程序有充分、准确的认识(例如调解程序的特点、调解员的职责、当事人随时撤出调解程序的权利),确保当事人在程序中有提出问题以及被聆听的机会,并负有确保调解公正进行的其他程序性义务。
三
我国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完善之路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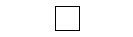
为更好地应对加入《公约》后面临的挑战,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和其他配套手段完善商事调解制度,为商事调解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以促进争议当事人更多地运用调解友好解决争议。笔者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制订商事调解基本法
在维持现有的法院调解、人民调解和专门性调解制度的同时,制订一部统一适用于国际、国内商事争议调解的法律。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相继就调解进行了专门立法。早在2008年,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就出台了欧盟《调解指令》,就调解相关事项向欧盟成员国提出了最低门槛要求,例如保证调解的质量,有条件地执行调解所达成的协议;2012年,我国香港地区制定了《调解条例》, 意图为在香港进行的调解提供适宜的法律框架,并避免损害调解原本所具有的灵活性点;[24]2017年,新加坡通过了《调解法2017》,为商事主体在新加坡进行调解提供更为稳定的法律保障。有鉴于此,我国也应当制订一部统一适用于国内、国际商事纠纷的调解基本法。
我国的商事调解基本法应确立两项基本原则。一是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UNCITRAL,2002年和 2018年版的调解示范法均贯彻了这一原则,以2018年版的示范法例:第1条第3款关于调解的定义强调了当事人“友好解决合同关系”,调解员无权将解决争议的办法强加于当事人”;第4条“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或变更本节的任何规定”;第6条第1款规定调解员应为一人,但当事人有权约定两名或多名调解员;第 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于调解之进行的规则或进行调解之方式;第12条规定,当事人向调解员声明终止调解程序的,调解程序于声明日终止;等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体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调解立法中。例如,新加坡《调解法27》第3条关于调解的定义强调,经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基于自愿。二是严格遵守保密原则。UNCITRAL 在解释设计调解程序相关条文之目的时表示:“基本考虑是力求平衡,既要保护调解过程的完整性,例如,确保满足当事人对调解保密的要求,同时又能提供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25]由此可见,保密及当事人意思自治是贯穿整个调解程序的原则性要求。不仅如此,保密原则也体现在示范法的具体条文中。例如,2002年版示范法第9条: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与调解程序有关的一切信息均应保密,但按照法律要求或者为了履行或执行和解协议而披露信息的除外。又如,该法第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调解人提供任何信息附有必须保密的特定条件的,该信息不得向参与调解的任何其他方当事人披露。前文提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调解立法也就保密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总之,保密不仅仅是调解法的义务性内容,更应作为调解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遵循上述两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国的商事调解基本法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适用范围。我国香港《调解条例》第5(1)条和新加坡《调解法2017》第 6(1)条对各自的适用范围作出了相似的规定,即既适用于在本地进行的调解,也适用于调解协议选择适用本法的情况。从《公约》第5.1(b)的规定来看,《公约》允许当事人约定和解协议的管辖法律。因此,我国的商事调解法宜就适用范围作出类似的规定,允许在境外进行调解的当事人通过调解协议选择适用中国的商事调解法律。(2)可调解事项的范围。一般而言,税收、海关等行政事项不应当允许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此外,我国其他部门法中已规定了特殊程序的事项也不应当适用商事调解基本法。(3)调解的保密性以及调解信息作为证据的可接纳性。前文提及,各国调解法一般都对调解程序和调解信息的保密有所要求,对有关主体在调解过程中所获知的信息之披露及该信息在后续程序中之使用进行限制。除立法明确列举允许披露的信息以及披露的方式外,还可授权法院在特定情形下允许有关主体进行特定信息的披露。(4)经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如前所述,此类协议的强制执行目前需经司法确认。如仅考虑《公约》在我国适用之需求,可通过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作出特别规定。然而,为鼓励非诉争议解决方式的运用,我国更适宜通过商事调解基本法对商事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作出规定。无论是国内商事和解协议还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均可申请法院予以执行。对于国际和解协议,根据《公约》的要求,仅可授权法院在《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情形下拒绝承认其效力。对于国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立法可以设置更多的限制性条件,例如调解程序需由经认证的调解机构或调解员主持。①(5)调解员的任职资格。鉴于国内、国际商事调解对于调解员素质的要求不同,商事调解基本法不宜对调解员的任职资格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可就任职资格作出若干禁止性的列举。
注释:
①例如,《德国调解法》第794条规定,调解协议可以经公证机构注册或认可后获得执行力,通过法院调解达成或经由国家认证的调解机构达成的调解协议自动具备执行力。参见:齐树洁《外国调解制度》,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6页。
(二)引导民间机构建立调解员认证机制
香港的调解认证机构 HKMAAL业主导式的单一认证模式,虽然设立该机构的建议最初是由律政司牵头设立的调解专责小组提出的,但官方并未实质性介入HKMAAL的设立,HKMAAL是由香港律师界、调解机构和仲裁机构联合推动设立的非官方性质的机构。新加坡的调解员认证机构SIMI由新加坡法律部根据《调解法 2017》第7条的授权进行指定的,但其认证机制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经SIMI认证的最高级别调解员可根据其与国际调解协会之间的协议直接申请成为后者的认证调解员。两相比较,香港模式更能保持和发扬调解的民间性特征。
在我国现行调解制度行政性色彩比较浓厚的背景下,我国在选择调解员认证模式时应更多考虑如何保持和发扬调解的民间性。因此,我国可在商事调解基本法中授权一个政府机构负责调解认证的促进工作,由该机构引导律师协会、仲裁和调解机构、行业协会等民间力量,合力推动统一的调解员认证机制的形成。鉴于国际、国内商事调解对调解员素质要求的差异,我国可以对调解员进行分层次认证,例如,分设国内商事调解员和国际商事调解员,对两者提出不同的认证要求。此外,个别行业也可以制定自己的行业调解员认证标准。
(三)制定调解员职业守则范本,将守则的遵守情况与调解员认证挂钩
鉴于我国调解员守则统一化、国际化程度不高的现状,我国应在国际调解协会的调解员职业守则的基础上,参考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地调解员职业守则的成熟经验,制定调解员职业守则范本,供各商事调解机构、律师调解员管理组织、行业协会选用,以促进调解员职业守则的标准化、国际化。
守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调解员接受任命前信息披露的内容及其真实性保证。例如,调解员的调解资质和相关经历,是否与案件存在利益冲突及冲突的具体情况,等等;披露的内容必须真实。(2)调解员独立性、公正性的制度保障。例如,调解员应即时披露新产生或新发现的利益冲突情形并提议退出调解程序,非经调解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员不得继续该调解程序;调解员应以独立、中立及公正的方式行事;确保当事人在程序中有提出问题以及被聆听的机会。(3)确保当事人对调解程序有充分、准确认识的制度保障。例如,调解员应告知当事人调解程序的特点、调解员的职责、当事人随时撤出调解程序的权利、对调解员不满时的投诉渠道,等等。(4)调解员的保密义务。除不得向第三人披露调解过程中所获悉的信息外,未经一方当事人的事前同意,调解员不得将该方秘密提供给调解员的信息披露给其他当事方。
我国调解机构现有的调解员守则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仅仅构成对调解员的道德要求,不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为此,可以借鉴HKMAAL和SIMI的做法,把违反调解员守则的情况与调解员认证相挂钩,建立对调解员投诉的评估机制。对于违反守则者,根据其情节的严重程度,给予书面警告、阶段性冻 结调解员认证资质和永久取消调解员认证资质等不同程度的处罚,以增强调解员守则的约束力。
(四)以调解员认证和职业守则为手段, 整合机构调解、律师调解和行业调解,形成一 体化的市场调解机制
除商事调解机构所提供的调解外,律师调解和行业调解也是我国目前市场化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相对有章可循,律师调解和行业调解则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规则或标准,使得其公信力大打折扣。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于2017年出台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尝试对律师调解进行规范。
如果能够将调解员认证和职业守则的要求统一适用于机构调解、律师调解和行业调解,将有助于破解当前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的困境。一名调解员,只要通过了相关的调解员认证,既可以被列入某一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员名单,也可以在通过了相关行业调解员认证的情况下成为行业调解员,如果该名调解员同时是律师,那么还可以提供律师调解。无论其以何种身份主持调解案件,均应遵守相应的调解员职业守则。如果商事调解机构、律师调解员管理组织以及行业协会均在前述的调解员职业守则范本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调解员职业守则,那么无论该名调解员以何种调解员身份进行调解,都将遵守同等程度的职业纪律约束,提供同等质量的调解服务。调解员认证的入门要求以及调解员职业守则的持续约束,将为当事人获得高质量的调解服务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四、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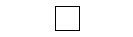
《公约》在商事调解国际立法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国承认和执行创造了可能,势将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条约之一。就我国而言,现行商事调解立法及配套制度的缺位或不足将阻碍《公约》在我国的运行。因此,为了避免我国法院被迫承认立法本无意授权调解予以解决的某些类型争议之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维护国际商事调解的正当性,提高商事调解的质量及其对商事争议当事人的吸引力,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我国应制定一部商事调解基本法, 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保密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就该法的适用范围、可调解事项的范围、调解的保密性、调解信息作为证据的可接纳性以及经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之可执行性等问题作出规定,以顺利衔接《公约》的相关规定,为商事调解创造完善的法律环境。
第二,引导民间机构建立调解员认证机制。我国可在商事调解基本法中授权一个政府机构负责调解认证的促进工作,由该机构引导律师协会、仲裁和调解机构、行业协会等民间力量,合力推动统一的调解员认证机制的形成。
第三,制订调解员职业守则范本,并将职业守则的遵守情况与调解员认证相挂钩,以促进调解员职业守则的标准化、国际化,强化守则的约束力。
第四,以调解员认证和职业守则为手段,推动我国一体化的市场调解机制的形成,使得机构调解、律师调解和行业调解遵守同等程度的职业纪律约束,能够提供同等质量的调解服务。
参考文献:
[1] 齐树洁. 外国调解制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31.
[2] UNIS. General Assembly Adopt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EB/OL].(2018-12-21)[2019-03-06]. http://www.unis.unvienna.org/unis/en/pressrels/2018/unisl271.html.
[3] 陆晓燕.“裁判式调解”现象透视——兼议“事清责明”在诉讼调解中的多元化定位[J].法学家,2019(1):101-111.
[4] 邓春梅. 中国调解的未来:困境、机遇与发展方向[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69-72.
[5] European Parliament,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irective 2008/5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08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EB/OL]. (2008-05-21) [2019-03-0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8L0052&from=en.
[6]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e of China. Cap 620 Mediation Ordinance[EB/OL].(2013-01-01)[2019-03-06].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0.
[7] OHADA. Uniform Act of 23 November 2017 on Mediation [EB/OL].(2017-11-23)[2019-03-06]. https://www.ohada.org/index.php/en/news/latest-news/2294-online-publication-of-the-new-ohada-laws-on-arbitration-and-mediation.
[8] Parliament of Singapore. Mediation Act 2017[EB/OL]. (2017-02-03)[2019-03-06]. https://sso.agc.gov.sg/Act/MA2017.
[9] 肖建华,唐玉富. 论法院调解保密原则[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4):138-146.
[10] Michael W BüHLER. Out of Africa: The 2018 OHADA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Law Refor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8(5): 517-539.
[11] 刘加良. 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实践误区及其矫正[J]. 政治与法律,2018(6):140-151.
[12] 孙巍.《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立法背景及条文释义[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52-53.
[13] 张圣翠. 论我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矫正[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1):42-49.
[14] Danny McFadden. Culture,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Mediation: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Communication Styles and Finding Mutual Understanding[J]. Asian Dispute Review, 2014(3): 132-136.
[15] Marianne Roth, Marianne Stegner. Mediation in Austria[J].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3(3): 367-378.
[16] 唐琼琼. 第三方资助纠纷解决规制模式的国际经验及思考[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6):140-152.
[17]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Mediation[EB/OL].(2010-02-08)[2019-03-06]. https://www.doj.gov.hk/eng/public/pdf/2010/med20100208e.pdf.
[18] HKMAAL. How to Become a Mediator[EB/OL]. (2018-06-26)[2019-03-06]. http://www.hkmaal.org.hk/en/HowToBecomeAMediator.php.
[19] SIMI. About The SIMI Credentialing Scheme[EB/OL]. (2014-07-15)[2019-03-06]. http://www.simi.org.sg/What-We-Offer/Mediators/SIMI-Credentialing-Scheme.
[20] UNCITRAL. 第二工作组(争议解决)六十八届会议(2018 年2月5日至9日,纽约)工作报告[EB/OL]. (2018-07-13) [2019-03-06]. https://undocs.org/zh/A/CN.9/934.
[21] Jonathan Crowe. Mediation Eth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Professionalisation[J]. Bond Law Review, 2017(5): 5-14.
[22] 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守则[EB/OL]. (2012-10-01) [2019-03-06]. http://www.scmc.org.cn/page67?article_id=83&menu_id=57.
[23] 上海金融商事调解中心.上海金融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守则[EB/OL]. (2016-10-01)[2019-03-06]. http://www.shjrss.com/about/72721/.
[24] Man Sing Yeung. The Hong Kong Mediation Code and Mediation Bill[J]. Asian Dispute Resolution, 2012(1): 27-29.
[25] UNCITRAL.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及其颁布和使用指南2002年[EB/OL].(2004-12-01)[2019-03-06].http://www.uncitral.org/pdf/chinese/texts/arbitration/ml-conc/04-90952_Ebook.pdf.
END
编辑:张 婷
校对:徐广娟
